“亚裔歧视”与宗教伦理:爱为何没能消弭仇恨与分歧

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与“仇恨亚裔”(Asian Hate)相关的事件着实在令人震惊,也催人反思。人们在赞叹人类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同时,这个世界似乎也充斥着对于不同和多样的敌视和仇恨,从肤色、观念到制度等等。对此,人们很容易想到爱的力量,想象着其渴求合一和共同的努力可以去克服差异所导致的各种形式的隔阂与冲突。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在人类文明中,一直存在着对于爱的颂扬和向往以至神往。可以说,爱,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情爱、友爱、亲情之爱以至神圣之爱,都展现其强大的力量。柏拉图的《会饮篇》、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以至《圣经》对爱的内涵都有丰富的表述。

当人们以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形式来歌颂爱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充分认识到爱的力量——尤其是宗教层面——与现世制度与原则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那里早已体现出来。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37-1920)和基督教哲学家兼神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对此做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在看到现代社会生活领域内在法则的差异时,韦伯特别指出宗教伦理(尤其是其爱的理想)在其中的限制。“我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每一个领域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各种宗教伦理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 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110页)。在他看来,“一种宗教伦理如果要把尘世组织成一个合乎宗教观点的系统化理性化整体,那么它与尘世社会制度之间的道德张力就会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具有原则意义。”(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717页)这种张力尤其体现在作为宗教伦理核心的仁爱思想上,“禁欲主义道德观以及神秘主义取向的兄弟之爱倾向,同作为一切政治制度之基础的支配机器的冲突,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紧张与妥协类型。“(同上,7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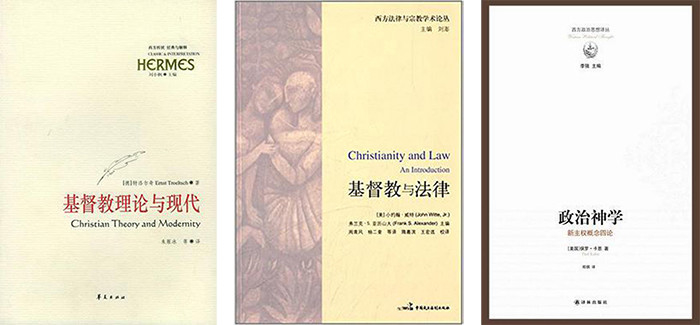
在“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一文里,韦伯集中论述了宗教性的无差别主义之爱与现世秩序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体现在经济、政治、审美、性爱以及知性等领域。一方面是各种价值领域愈加理性化和独立,另一方面是宗教伦理要求——尤其是普遍主义的同胞意识——与此世原则有着严格区别并抱着对之更高的期待,这样一来,宗教伦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便不可避免。“当宗教与政治领域皆完全理性化时,二者间也就更加无法无法兼容,因为政治,与经济不同,会在决定性要点上成为宗教伦理的直接竞争对手。”(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 477页)就审美领域来说,“一边是宗教伦理的升华与救赎要求,另一边则是艺术之固有法则性的开展,两者之间趋向一种日渐增加的紧张关系。”(同上,486页)
与韦伯处于同一时代并与他有着不少思想互动的特洛尔奇也同样认为“基督教伦理彻底的非政治化性质”(特洛尔奇著,朱雁冰等译,《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华夏出版社,2004年,306页),或者说,“不存在一种从本质上直接出自基督教观念的政治伦理” (同上, 304页);作为基督教伦理的核心观念,爱上帝与邻人“均非政治原则”(同上, 304页)。基督教伦理与艺术、科学、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有所不同,它必须承认与它并存的其他领域自身的伦理原则。即使特洛尔奇认可基督教伦理与其他领域的伦理原则的相对分离,与韦伯一样,他对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性。韦伯关注人的尊严、现代经济生活的 “气质”(职业伦理)、政治行为的责任伦理等,而特洛尔奇也坚持认为基督教的观念可以其独特的价值影响不同的道德结构,尤其是其博爱思想已转化为共同的人性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从而产生影响。虽然国家有其自身独立的道德观念(如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感),但是,“基督教伦理也为国家提供道德观念,国家能够以此类观念补充和深化其纯粹的政治道德。”(同上,314页)
特洛尔奇承认,“整个基督教伦理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在心灵圣洁和爱邻人的纯粹宗教理想(此时它对自然生活漠然置之)与控制、净化、提高自然世界的内在理想之间摇摆。”(同上,315页)看来,这种基督教伦理的宗教理想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距离与交织正是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正是其宗教性质的绝对性使得其必须认可现世各种领域法则的相对独立性并同时负有对其道德结构的提升和转化责任;这种进路在现代世俗化社会——以社会分化和多元化、宗教的式微为主要特征——考量宗教的文化和社会功能转型尤为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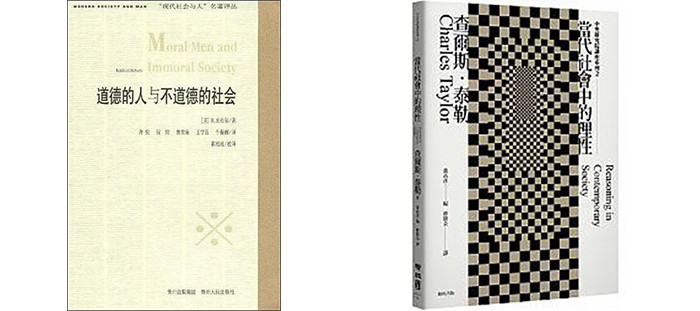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的韦伯与特洛尔奇洞察到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与自主从而对宗教/基督教伦理与现世关系做出“紧张性”的思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透视了爱的价值与限制。在接近的时代,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以类似的方式触及了这一主题,并集中体现在他对“爱与正义”的关系思考上。从基督教的人性观出发,尼布尔考察了他所处时代的各种宗教和世俗自由主义,对于社会、人性的理想乐观态度以及各种进步和无止境的完善观念做出了批判性的反思,尤其是尖锐地批评了基督教道德主义把爱的律令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他认为,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和宽容性的爱是基督教伦理的精华,只能作为“宗教的最高想象力”,“只能在亲密的宗教团体中实现”(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49页)。因而,“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全部力量绝不可能都用来建设正义的社会”(同上, 49页)
对于尼布尔来说,群体的事务、政治和经济的结构需要由具体的正义原则来规整和处理,由此确保其应有的秩序。在此,“爱要表现自身就十分困难,复杂的社会情况要求进行复杂的理智分析,由此必然会挫败仁慈冲动的力量。”(同上,59页) 然而,对于政治道德而言,爱的理想与正义的原则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或者说,爱的理想与超验性赋予了正义特定的内涵(如平等的原则),让我们看到单纯依赖爱的理想原则之不可能性的同时,看到单纯依赖政治秩序原则的局限性。爱的理想不应取代现世正义,但意示着正义的相对性,并负有纠正、转化和提升正义的责任,让我们对正义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在尼布尔身上,我们听到了一种特洛尔奇式的回响:“每一种追求社会公正的真正激情,总是包含着宗教的成分。宗教总是使公正的观念掺杂着爱的理想,从而防止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公正观念由于伦理成分的丧失而变为纯粹的政治观念。”(同上,49页)

基督教伦理(尤其爱的观念)与现世秩序与规范(尤其是正义原则)的分别及动态关系,在当代学界,一直得到持续的关注和探究。这一主题不仅在基督教学界,而且在其他相关的学科领域如哲学、政治学、法学都是重要的话题。著名基督教哲学家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在其新著《爱中的正义》(Justice in Love, Eerdmans, 2015)试图超越尼布尔对于爱与正义之冲突的阐释,从“爱人如己”的命令中阐发出对于自身和他人价值的尊重及其中蕴涵的对于正义的寻求。从法学角度也出现了不少关于基督教之爱与法律议题题关系的思考。墨菲(Jeffrie G. Murphy)在“基督之爱与刑罚”中提出了“为什么思考刑事问题需要关注爱的价值?”这样发人深思的问题。他关注的是体现爱的宽恕精神与刑法和刑事正义的关系,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博爱并不禁止适用刑罚。它所禁止的是出于仇恨或者其他报复心而施加的刑罚。”(墨菲,““基督之爱与刑罚”,载小约翰. 维特、弗兰克.S. 亚历山大主编,周青风等译,《基督教与法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 190页)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圣爱、正义与法律:基督教之爱如何塑造法律?》一书,结合基督教思想传统和当下的具体议题(如长者关怀、公司、知识产权、移民、国际政治等)探讨了爱的观念在当代法律中的挑战与意义。(Robert F. Cochran & Zachary R. Calo, eds., Agape, Justice, and Law: How Might Christian Love Shap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简要回溯一个世纪来欧美学界在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诸多学科领域对于宗教伦理(以基督教伦理之爱的观念为典型)与现世秩序与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动态关系的最后,我想到了耶鲁法学院卡恩教授(Paul Kahn)在其《当法律遇见爱:解读》一书中所发出的警醒:“一个有爱的灵魂拯救不了国家”( 保罗.卡恩著,付瑶译,《当法律遇见爱:解读》,法律出版社,2011年, 230页),因为,“任何政治秩序中,政治本身的残酷逻辑与爱所独有的价值之间都存在着冲突。”(同上,237页),但是,同等重要的是,“最高的真理和真正的自由,存在于法律之外”(同上,4页)。法律之外,是长阔高深的爱的天地。不止如此,爱的独特性是一把双刃剑;爱的价值与法律、政治逻辑的分野与冲突并不意味着爱与它们无关。卡恩在其他地方说道:“在政治中,像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那样,我们同时需要爱和正义,但那种需要并没有使它们变成同一个东西。” (保罗.卡恩著,郑琪著,《政治神学:新主权概念四论》,译林出版社,2015年, 135页)
当我们面临着诸多差异和仇恨,我们看来必须珍视多样性的价值(泰勒甚至认为对于不同宗教与世界观的尊重也是“博爱”精神的体现,见查尔斯.泰勒著,萧高彦编,蒋馥朵译 ,《当代社会中的理性》,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2-63页),也必须重拾爱——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理想和强大,但也必须同时清醒认识到爱的脆弱,认定复杂严酷的社会政治结构需要足够的理智分析和相应准则。真正的爱的力量在于直面现世的分化以至对宗教的排拒,在于以其独有的意义源泉去发现现实世界任何理性原则包括正义的限制并指引其方向。
(本文原标题为《爱的坚强与脆弱》,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