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阿尔特:人在痛苦中寻求自证|书评

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一本近百年前写就的小说?这就好比探问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在当下的意义何在。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巨变,人身上固有的惰性和邪恶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今天,我们阅读罗伯特·阿尔特的原因也在于此。与百年前的阿根廷人相比,我们变得更高尚了吗?我想并没有。罗伯特·阿尔特在他的小说中写尽了人身上阴暗的一面,他将人物抛入痛苦的深渊,以此探寻存在的意义。
撰文丨把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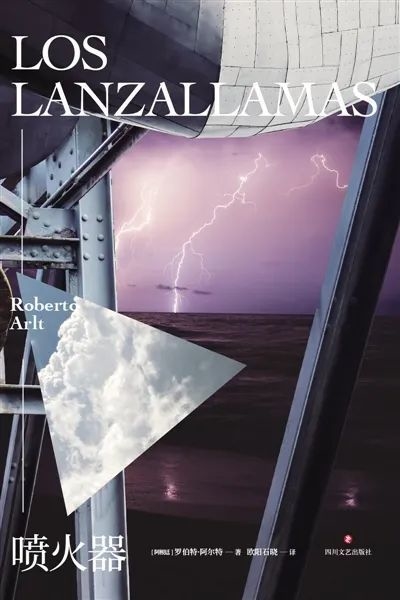
《喷火器》
作者:(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
译者:欧阳石晓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1
革命的深化
《七个疯子》构想出一个疯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几位身份殊异却同样被生活逼入绝境的“疯子”,“名正言顺”地想要为现实世界重新立法,以反抗现有的秩序。《喷火器》承续《七个疯子》而来,继续以埃尔多萨因的视角讲述疯子们在占星家的联合下,继续深入实践社会革命,并最终失败的故事。在《七个疯子》中,“占星家”构想创建一个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特色的新型社会。革命将通过妓院获得收入,收入投入到革命基地的建设中,然后招募新成员,来学习无政府主义策略。创建妓院的任务落在了埃尔多萨因的身上,他在《七个疯子》的结尾杀死了总是羞辱他的巴尔素特,从而获得了两万比索。这笔钱成为“占星家”筹建秘密社会的基金。
到了《喷火器》中,“占星家”对社会革命的具体落实有了更为深入的构想。首先是如何组建革命基层的问题,“占星家”认为得从情感基层和能量基层两方面入手。“情感基层是由那些没有能力进行能量活动或严重的社会罪行的人组成。” 由于情感基层效果有限,重任被寄托在能量基层上。能量基层由年轻男人组成,他们在公开场合假装遵从统治政权,拥护资产阶级,背地里则实行极其严重的社会犯罪。革命最后的行动是制造光气,以此作为武器进攻军事区,从而“完全、彻底、绝对地消灭所有那些捍卫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学员们在革命学校将学习如何制造毒气和使用毒气。
“占星家”的社会革命并非通过启发民智来唤起阶级意识,然后反抗资本家。他构想出新的革命路线:掌控军权实施独裁政体,以此唤醒民众心中的愤怒,从而让民众自觉选择变成反军国主义者。“占星家”以细菌入侵身体为例形象阐释了这个构想:军权统治如同在一具患病的身体里引起另一种疾病,从而消灭真正有害的微生物。

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出身于阿根廷普鲁士移民家庭,成长于城市拥挤的廉租房。16岁离开家后,他当过书店职员、铁匠学徒、油漆工、焊工等,直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报》任职,1942年,因急病去世,有《七个疯子》《喷火器》《愤怒的玩具》等小说和戏剧作品数部传世。
2
疯狂的代价
在“七个疯子”里,“占星家”最为疯狂、也最为清醒。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其他“疯子”成为了他手中的棋子。“占星家”认为,发起社会革命得靠骗子、倒霉蛋、杀人犯和小偷,以及那些绝望且痛苦的歹徒们。于是他找到了埃尔多萨因、皮条客、巴尔素特、伊波丽塔、淘金者、少校、律师、药剂师等人物,来实现自己的革命梦想。他尤为青睐女性,认为“女人是真相的开端和结尾”。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允许引诱失明的少女到妓院工作。而男人则是“懦弱、狡猾、吝啬、淫荡、多疑、贪婪、馋嘴”的化身,被资本主义政权和无神论所毁坏。
《喷火器》的最后几页充满着一种忧伤的气息。埃尔多萨因在火车上自杀,成了人们唾弃的对象,他的事迹也被登在头条来提升报纸销量;巴尔素特因为供出同谋而名声大噪,跑到好莱坞成为电影明星,受到影迷热情的追捧;而伊波丽塔和“占星家”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埃尔多萨因能想到他的举动要付出这种惨痛的代价吗?他或许到死也没明白自己工具人的身份。就像任何流产的革命一样,革命者悲壮的举动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细水长流中。“七个疯子”组织的秘密革命最终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偶尔占据报纸的一角。
看来,罗伯特·阿尔特是悲观的,他并不想象疯狂的革命会得到实现;同时他也是清醒的,因为疯狂的革命当然不会得到实现。不然这就不是现实世界,而是童话故事了。但是,在这种疯狂的革命构想背后,罗伯特·阿尔特实际上揭示出现实世界里诸多隐秘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占星家”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代表着罗伯特·阿尔特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宗教的缺席是这个世纪的不幸,它毁掉了我们的理智,导致我们在体外寻找事实上藏在潜意识的神秘之中的东西”。占星家之所以发动社会革命乃是为了拯救失去信仰的不幸之人,让他们重新认识神圣的真理。
这当然是事实,尤其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信仰的缺失。除了 “上帝死了”,《七个疯子》和《喷火器》还践行着尼采的“超人哲学”。小说里有一处这样写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超人,那个超人是最大限度的意志力,超越所有的道德规范,执行最恐怖的决议,带着最纯真的愉悦……类似于天真的残酷游戏。”“七个疯子”的举动也是超人的举动,他们通过行动来获得生命力和能量。阿尔特继续写道,“当人们意识到灵魂已陷入文明的粪坑中时,他们必须在被淹死前掉头。事实上,是懦弱和基督教让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病入膏肓。”这让我们想起尼采所言的“价值重估”,尼采在《敌基督者》中传达着相似的观点:基督教徒的怜悯扼杀了人的生命活力,这是基督教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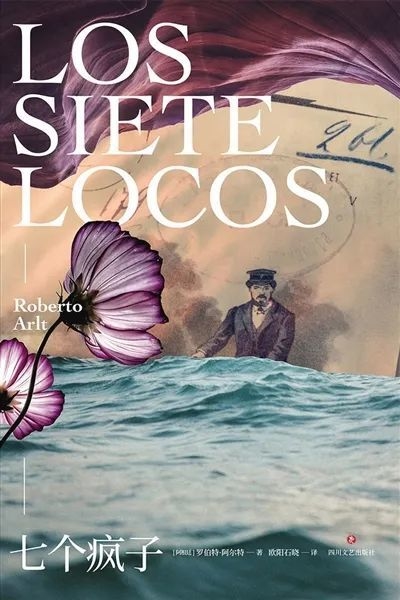
《七个疯子》,作者:(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译者:欧阳石晓,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
3
一则深刻的社会寓言
这么看来,罗伯特·阿尔特大概看过尼采的书,并从中得到了一些滋养。同时,这也让我们把罗伯特·阿尔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在一起。据说,在所有的心理学家里面,尼采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学到了一点。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否认自己是心理学家,称自己仅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任务是“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自传、书信及记事本摘抄》)。《七个疯子》和《喷火器》里的世界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世界的重演。当人不再处身于一个宗教的世界,彻底迷失方向,剩下的便唯有痛苦和伤害。
埃尔多萨因像极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罗伯特·阿尔特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底迷失的灵魂,试图在最堕落的生活中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伟大和崇高。”妻子艾尔莎也指责他“痛苦是你自找的邪恶的快感”。埃尔多萨因在堕落的过程中体验着一种超强度的快感,在遭受苦难的过程中了解世界的真相。一个以寻觅痛苦来自证存在的人,这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深刻发现吗?占星家早就看穿一切,他称埃尔多萨因是“享受侮辱的倒霉蛋”,“代表着受着苦、做着梦的人性,全身甚至连胳肢窝都陷入到了屈辱之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了摆脱痛苦,最终在蛊惑之下走向了绝境。
在《喷火器》的开头,罗伯特·阿尔特写到埃尔多萨因的偷窃,能够为我们理解埃尔多萨因的受虐心理提供帮助。埃尔多萨因偷窃,除了减轻生活的负担之外,同时也是为了在犯罪过程中找到惊喜,“划破日常生活的单调与无聊”。“当他想到可以偷老板钱的时候,感受到发明家一般的快乐”,埃尔多萨因从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了满足感。埃尔多萨因加入组织,策划杀掉巴尔素特,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在犯罪中获得存在感。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找到的犯罪动机:证明自己是超人。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的人物走向救赎,罗伯特·阿尔特则留给埃尔多萨因一阵嘲讽的笑声。
《喷火器》是一则深刻的社会寓言。罗伯特·阿尔特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借助生动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一群“疯子”的形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而腐败的运作机制(“当下社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对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剥削之上的”),同时也透析出人性深处的惰性与邪恶。这样的小说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