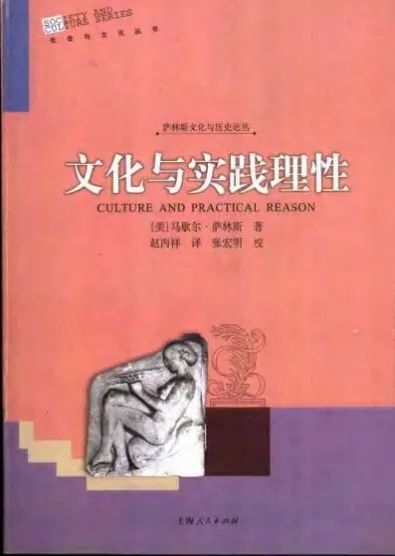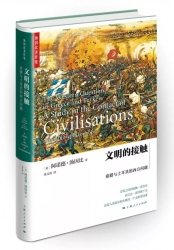王铭铭、赵丙祥、梁永佳、郑少雄|纪念马歇尔·萨林斯

2021年4月5日,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去世。他是西方人类学最后的大师。
三联书店自2000年开始持续关注、出版萨林斯作品,如《甜蜜的悲哀》《石器时代经济学》和《人性的西方幻象》。萨林斯与其学生大卫·格雷伯合著的《论君主》也正在翻译中,即将出版。
王铭铭先生自上世纪末即与萨林斯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在他的组织下,多位青年学人先后翻译出版了萨林斯的重要作品。值萨林斯先生辞世,王铭铭与赵丙祥、梁永佳、郑少雄等中国两代学人特为文纪念,授权“三联学术通讯”刊发,向这位人类学家致敬。

马歇尔·萨林斯
(1930.12.27—2021.4.5)
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家族,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从博士论文研究开始,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并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文化,进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种观念的缺失。1956 年至1973 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73 年以来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时代经济学》、《文化与实践理性》以及《历史之岛》等,这些著作对晚近西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1
我所认识的萨林斯
|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复活节刚过,4月5日,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老先生在家中悄然辞世。
我们刚刚失去的这位人类学大师,1930年12月27日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家庭。他在密歇根大学接受本科和硕士教育,24岁时,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人类学家傅瑞德[Morton Fried]),三年后,年仅27岁即当上了密歇根大学正教授。而立之年,萨林斯已是一个新学派(新进化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萨林斯赴巴黎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得益于结构主义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指导。返回美国后不久,萨林斯的学术观点发生了剧变。他离开密歇根大学,转任芝大人类学系教授之职,直到1997年以格雷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杰出荣休讲座教授(Charles F. Gr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meritus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的衔头退休。
与他的同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一样,萨林斯是“文化”概念的守护者。然而,与格尔兹不同,他没怎么征引过美国化的韦伯思想。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波亚士式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古典文明研究。他在大量著述中综合了这些思想资源,使其在与历史和民族志的相互融合中获得新活力。
萨林斯对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民族之亲属制度、政治结构及自然观念持续关注,他总是凝视着这些体系的思想形质和近代遭际。借助于其在理论和“土著宇宙论”方面的素养,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生物学、现代自然观念的批判影响广泛。
1960年代萨林斯已顶顶大名,但他却选择将1972年看成一个“开端”。那年,他出版了《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通过界定“原始丰裕社会”,颠覆了进化论的历史意象。在该书中,他还复原了“互惠”、“债”等交换类型的复杂内涵。1976年,他出版了《社会生物学的运用与滥用》《文化与实践理性》两本书,揭露了社会生物学的西方(特别是霍布斯)人性论本质,批判了文化的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解释。稍后,萨林斯对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界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之说,提出了重要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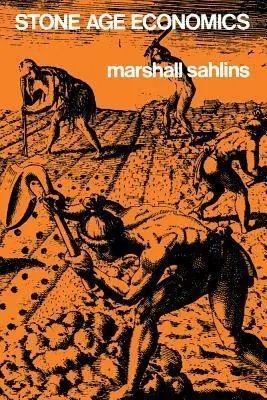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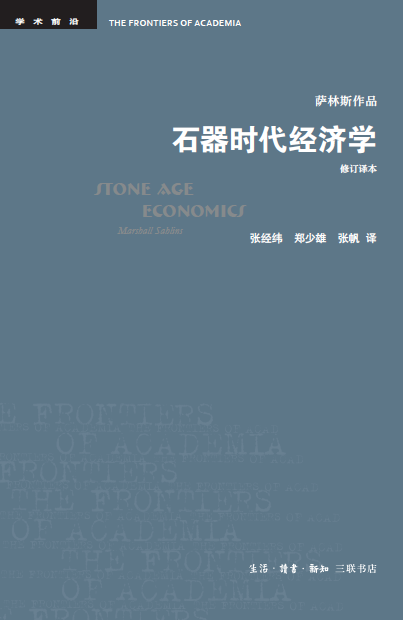
《石器时代经济学》
(英文版初版于1972年,中文版出版于2009年,再版于2019年)
知命之年起,在一系列有关太平洋“岛国”文化接触的历史人类学作品中,萨林斯呈现了同时展开结构与事件、宇宙观与历史进程研究的一种可能。为了揭示帝国主义“文明教化”的传播限度,他强调了“土著传统”在近代史中的绵续力。到了1990年代中期,萨林斯摸索出了一条比较和关联“土著传统”与“西方思想”的独特路线。在1996年发表的《甜蜜的悲哀》这一宏文中,他系统论述了非西方宇宙论与本体论对于文明“自知之明”之形成的启迪。
古稀之年,萨林斯出版了一部厚重的自选集《实践中的文化》。该书汇编了他在40年间所写的14篇代表之作。而此后,他依旧笔耕不辍。他对人类学经典领域表现出越来越集中的关注,著述大量论著,对作为文化的历史、亲属制度、王权诸论题加以深入评注。
我还是本科生时,萨林斯已是“大牛”,也进入了国内人类学者的视野。
1984年2月16日至3月10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萨林斯作为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代表团十位成员之一来华,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等机构。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上学。萨林斯一行在厦期间,我与同学们被系里组织去听座谈。萨林斯虽不是团长,却在座谈会上唱主角,他开场即称,“来到南方很高兴,因为这里的学者对人类学有兴趣。我们代表团去过的其他院校,发现在那些机构工作的学者们对人类学毫无兴趣,只关心如何做实用型研究”。他讲的其他话我不大记得了,但这句话我却总是记忆犹新。
到1988年,萨林斯已开始论及中国文化。那年春季,他获得一份殊荣,前往大英学院做拉德克里夫-布朗纪念讲座(Radcliffe-Brown Memorial Lecture),在讲座中,他花了相当长篇幅论述中国古代宇宙论的世界主义特征。到了夏季,萨林斯应邀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访学,除了利用机会去参观他感兴趣的名胜古迹之外,还开设一门课程。据他当时的助手邵京说,听课的年轻学子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大学),课程内容是芝大人类学“Systems”一课的“缩减版”,在四五周内完成。萨林斯从《圣经》、《上帝之城》讲到启蒙运动,再讲到社会科学,如当年听过该课的青年思想领袖甘阳所言,那是一门西方文明入门课。萨林斯如此授课,意图是将启蒙运动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从哲学和科学的圣坛推移到宗教文化和宇宙论的系列中,使之与非西方文化处于同等地位。
很可惜当年我没有机会上这门精彩的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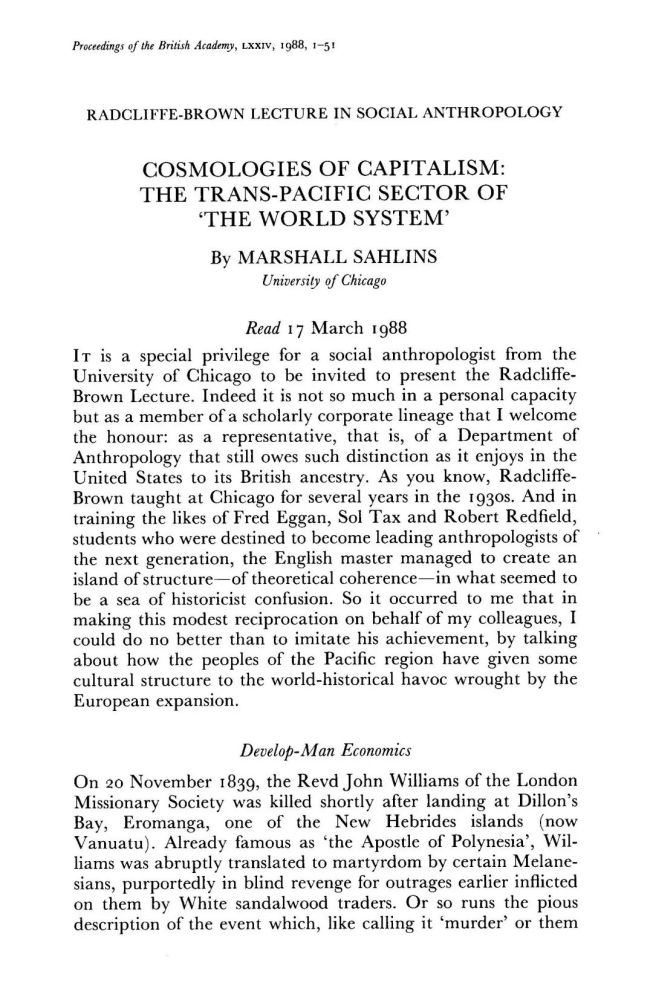
1988年,萨林斯在大英学院做拉德克里夫-布朗纪念讲座,
题目为《资本主义的宇宙观》
1980年代,我算是翻过萨林斯与塞维斯合编的《文化与进化》及所著《石器时代经济学》。1988年,我在伦敦留学,短暂关注过他与“世界体系学派”之间的争议。不过,当时英国人类学依旧轻视历史,结构主义思潮也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淹没了,萨林斯的“文化论”没有什么市场,我也就悬置了自己的兴趣。我比较集中关注萨林斯的作品是在回国工作两三年后。
我所在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是费孝通先生创建的。费先生在国际人类学界声誉很高,研究所得益于此,定期收到国外寄送的“权威期刊”。当时我定期到研究所图书资料室阅读《当代人类学》杂志。1996年,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一文(此文阐述的内容,与他在北外上的课有不少重叠之处)刚出,我便为其广阔的视野和大胆的诠释所震撼。我决心阅读更多他的作品。
也正值此时,萨林斯访华,由其弟子吴一庆陪同,从昆明绕道广州来京,我陪他在研究所当年的小灰楼二层会议室座谈。他得知北大人类学有成长苗头,非常高兴。
次年12月,费先生约见北大校长,请求其支持研究所人类学学科建设,包括组织一次大型学术活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召开“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会议与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作为研讨班的具体办事者(“班主任”),我受命邀请海外人类学家与会。我自然请了萨林斯,而他也欣然前来。萨林斯在北大做了题为“何为人类学启蒙?”的主旨演讲。我们之间在研讨班课余有不少闲聊的机会。他读了我一篇文章跟我说,“你的观点很像我儿子彼特的”。
对许多事,萨林斯都风趣、幽默、富人性地加以评论,这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与他的联系频繁了起来。我约研究生胡宗泽一道翻译了《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该文作为一本小册子,20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还约了赵丙祥、蓝达居、张宏明等年轻学友,请他们翻译《文化与实践理性》《历史之岛》《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三本书(我将这三本书编成“萨林斯历史与文化论丛”,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

《甜蜜的悲哀》(三联书店,2000)
2000年1月至6月,在萨林斯的安排下,我赴芝大,担任人类学访问教授,在研究生中开设《人类学中的中国问题》一课,期间,亦多次利用“蹭饭”机会就教于他老人家。
接近了这位知识界巨匠,我看到,他从不拘泥于所谓“民族志”,而是一位社会思想家,他致力于凭靠结构神话学、社会学和历史的汇通,焕发文化人类学的活力。对于当年成为“时尚”的后现代主义,他抱怨颇多。他常去听学术讲座,听完后,却总是反复提同一个问题:“文化哪里去了?”萨林斯非常担心,某些“学术时尚”正在瓦解人类学的知识大厦,而这些“时尚”,本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们都源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其包括功利、个人、权力观念在内的“恶之花”,本该是人类学者必须反对的。我在哈佛大学和芝大做过一个讲座,以“天下”为例,从“远东”世界思想出发,梳理人类学史的“另一条脉络”。在哈佛,来听的教授中有个后殖民主义者,他批评我没有关注“他者认识”的权力问题,我在芝大做完讲座后,却得到萨林斯的相反评论,他说,“你这篇人类学史比既有的都要好,我们这边的人类学史只谈西方的故事,太烂!”萨林斯送了我一本1993年发表的《别了,犹豫的热带》一文的抽印本。在文中他指出,不要以为随着所谓“时间”的推移(或者说,随着“热社会”的扩张),非西方“冷社会”的文化将会丧失生命力;相反,非西方“冷社会”的文化不仅或从现代“世界体系”汲取重生的养分,而且,其蕴藏的思想系统,对于西方文明的“自知”和“节制”,都是极具指导意义的。我自知,他对我的讲座有好评,并不是因为我真的讲得好,而只不过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西方之外的“世界思想”的到来。
在芝大期间,萨林斯还送我一未定稿。该文是有关波利尼西亚战争的,文中,萨林斯将战争视作关系的一种。2004年,他将相关论文汇编在《向修昔底德致歉》这本“戏说”波利尼西亚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中。这本少见的人类学与古典学的“综合文本”告诉人们,古希腊修昔底德战争中心的历史观仍旧影响着当代西方的世界活动,它使这些活动重现作为人的“兽性”之表现的深层战争观念,而波利尼西亚的“战争理论”则不同,它重关系,与“兽性”的人性论有根本区别,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古希腊文明。
萨林斯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通过写作揭示暴力与仇恨的西方宇宙观根源,而且还通过社会活动,对美国发起的越战、伊拉克战争公开表示抗议。另外,我抵达芝大时,他刚在线上和线下散布了自己的《心灵之命与肉身之爱》一文。借助这篇“檄文”,萨林斯推翻了一项旨在使芝大变成一个以管理学为中心的富有学校的计划。
谈到与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大学观”所做的这些斗争,萨林斯脸上总是露出自豪的表情。
他退休后,除了著书立说外,还自任一个出版社——Prickly Paradigm——的“执行主编”。这家出版社只出版小册子,特别是文体不拘一格、对21世纪有根本价值的作品。
从芝大回国后,因各种原因,我有若干年极少有机会组织学术活动。不过,2006年起,我兼任中央民大“985工程”一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之职,便开始频繁召集学术讲座、对话、研习活动。我约萨林斯来讲座。2008年9月,他和夫人得以成行,来到北京,还去上海、福建走了一圈。在北京,萨林斯展示了他对“陌生人-王”、“跨文化政治中的整体与局部之间关系”的诠释。在上海,他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邀,讲述了其即将出版的《人性的西方幻象》一书的内容(青年才俊刘琪、刘永华、罗杨翻译了这些讲座,后来我将它们编入《中国人类学评论》杂志第九辑中)。在福建,在我的“导游”下,萨林斯参观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他对前者陈列的古代中外文明交流史文物印象尤其深刻,感叹说,“这个小小的地方博物馆太重要了,足以表明西方近代世界史的观点是彻底错误的”。

2008年,萨林斯在复旦大学
2008年以后,萨林斯更多参与欧美的学术活动,而没有再来华访问,我则一直关注他的动向。2013年,我突然得知,他又一次成了舆论的“焦点人物”。在担任2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后,萨林斯突然放弃了院士职务。他发表公开声明,称他辞去院士的理由有二:其一,美国国家科学院居然选了一个曾经暗中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类学家为院士;其二,那些年国科院与美国军事部门有密切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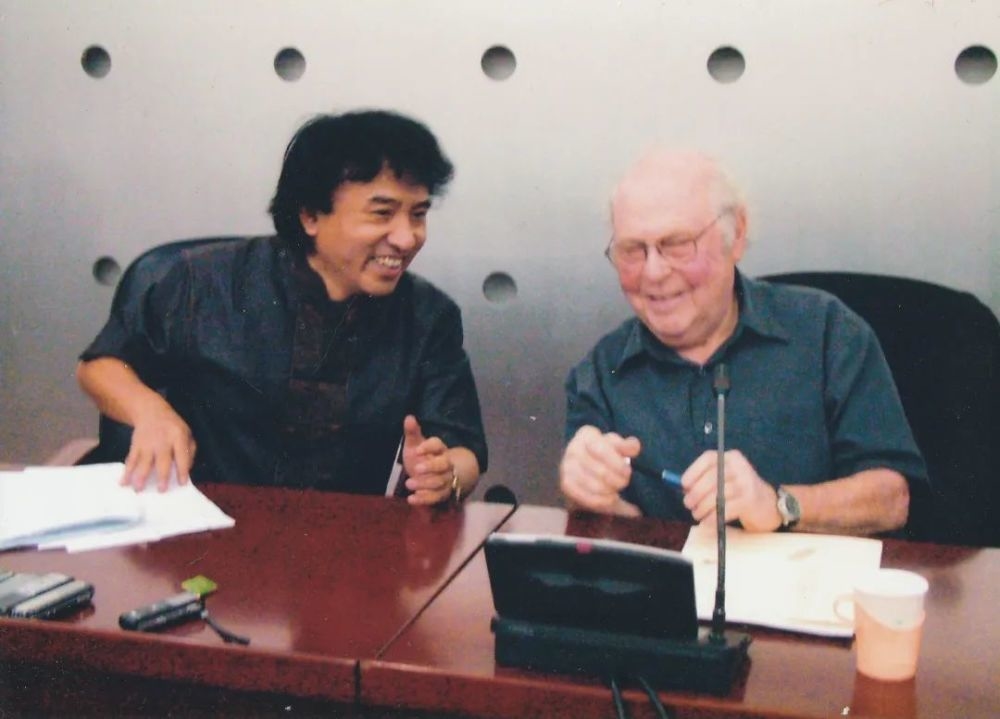
2008年,萨林斯在北京,左为王铭铭
2019年,我的另一个忘年交、杰出人类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戴木德(Frederick Damon,我称他“老戴”)教授来信邀请我去参与一个有关环太平洋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我回信说,假如他能在邀请函上也写上我的芝加哥行程,那我就一定去。我的私心是,要借这个机会去探望年近90的萨林斯。老戴果然应允......抵达弗吉尼亚大学,我即刻写了封信给萨林斯报告自己的行程安排,萨林斯“秒回”,并贴了一份附件,这附件是他正在开始写的一本新书的导论。这本书属于他计划完成的有关大洋洲文化与思想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它的书名是《魔幻宇宙的新科学》。
在芝加哥,我们首先在一家餐馆相聚,接着去了他那座位于芝大学校园内的别墅喝茶。那时萨林斯已是耄耋老人,手有时不免颤抖,但他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风采依旧。在他家喝茶时,他兴奋地展示了他新购置的一台阅读仪。他眼睛花得厉害,说靠这个大阅读仪,他便能很好地读书了。我说我的眼睛也花了,他睁大眼睛跟我说:“要注意了,这事很重要,别像我一样......”聊天时,我提到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大英学院见过他的爱徒、著名人类学家葛雷博(David Graeber)。萨林斯非常高兴,立刻建议说:“.....这次你一定要去Seminary Co-op书店,那有个架子把葛雷博和我的照片放在一块儿,还有我们的书!”在书店,我在萨林斯近期写下的文字里看到过一两行字,上面说,他的学生葛雷博如同他的老师一样,教给他许多东西。这令我难忘。萨林斯不善伪装谦卑,而对他的这位爱徒,他的每个字,似乎都出自真心。令人痛心的是,两个多月后(2020年9月),年仅59岁的葛雷博突然逝世。

David Graeber(1961.2.12—2020.9.2)
离开芝城前,萨林斯夫妇在他们平日爱去的中国餐厅请客。饭后我们就告别了。
去年12月27日,萨林斯的儿子彼特为他在网上安排了一个90华诞生日聚会。我应邀参加了。萨林斯身体不舒服,没有参加。但聚会两天后,他给大家发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你们在我生日那天,说了许多溢美之词,我非常感激。你们的慷慨陈词使我康复了起来。现在我每天都在写那部得到我的全部人类学生涯启迪的书。”这本书指的就是有关大洋洲文化与思想的三部曲。尽管萨林斯敦促众位友人与他多写信谈自己的研究计划,但我们更期待看到的是他老人家的巨著。令人哀伤的是,他仅完成了三部曲的第一部,就仙逝了。
萨林斯一生的事业是人类学。在我的感知中,这门学科在国内高等院校内发育并不健全,但最近它在“学术体制外”相当时髦:它正“搔首弄姿”,魅惑着不少好奇的年轻人。遗憾的是,不知怎么地,国内的“行内人”,若不是对这位智者全然不知,那也往往只是表面知道。我们中有不少人染上了学术功利主义习气,即使是那些还算是有想法的人,想必也会以萨林斯的反功利主义人类学为敌。我们中也有不少人染上了“追风”习气,它们能对像萨林斯这样的老一代“敬而远之”就算不错了。加之,时下不少“人类学明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出于各自局限和需要,出于无知或有意,在演示人类学的魅惑力之时,往往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像萨林斯这样的“无须了解的过时的老家伙”,必然不大会被提到。
然而,这些现象从来都没有颠覆我对萨林斯的“信仰”。
得知萨林斯过世的不幸消息,老戴迅即给我写了封信,他说,此时他正在给本科生上课,正好提到我及我与萨林斯的关系......老戴还说,“几个月前,有个萨林斯90华诞线上庆贺会,那时我才想起,必须同老人家说,我从与你及你的学生的联系中学到很多。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机会来写这封信。对他的过世,我感到非常悲伤......我非常伤心没有告诉他咱们一起做的那些事”。老戴提到的我和我的学生做的事,大抵便是指我们一起参考萨林斯“无用之学”做的一些工作,而他提到的“咱们一起做的那些事”,人们知道得非常少。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我热衷于同人类学界研究中国以外区域的学者交际;老戴这位数十年如一日只研究美拉尼西亚的大人类学家,便是其中之一。“隔行如隔山”,与他们聊天,和读萨林斯的波利尼西亚和印欧故事一样,理解上其实有不小的难度。然而,我相信,这种跨越“民族志学术区”的对话,对于包括华夏在内的欧亚诸文明“自知之明”的再生成,将有重要启迪。我也相信,老戴说的“咱们一起做的那些事”指的就是这类事。
2008年萨林斯在华期间,社科院罗红光教授带领他的摄影团队前往泉州与我们汇合,并建议我与老人家举办一场“学者对谈”,由他们进行全程拍摄。萨林斯欣然同意,并建议围绕“We are one of the other”(“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这个主题来讨论(对谈于9月30日在泉州后城一家老茶馆中举行,由罗杨根据录音整理并翻译,形成文字稿,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十二辑,音像版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一语,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老戴所说的“咱们一起......”意思相通。它指向“关系主义文明论”所旨在抵达的境界。在萨林斯通过辞世进入人文科学先贤祠的日子里,这句话变得格外意味深长。
02
何为萨林斯式启蒙?
纪念马歇尔·萨林斯教授
| 赵丙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4月7日早晨,忽见师友微信圈里发布了马歇尔·萨林斯教授于5日辞世的消息,有些不知如何之感。因他辞世的5日那天,我也正与家人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仪式,而本日又见多位朋友颇有“一个时代终结”的感叹,一时不知该如何言说。以九十一岁耄耋之龄辞世,按中国人的标准看,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悲伤之事,但师友们的怀旧之叹,以及对于亦如我这般从他的著述中受益的译者和读者,“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怀着这般心绪来缅怀一位前辈,也自是人之常情。不过,转念之间,我又觉得,按他的一贯作风,尽管在祖籍上与契诃夫可算同乡,萨林斯大概也不会愿意看到我们这些活人以“萨哈林岛民(Sakhalins)”的悲戚方式来悼念他吧。
萨林斯教授的作品已有七、八种汉译本,还有一两种正在翻译。若论对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人类学家启发最大的人类学家,萨林斯当属其中之一。尤其是他在结构和历史之间所作的融合工作,对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也不算小。我学习人类学之初,萨林斯、格尔兹等人的作品开始被迻译进入汉语世界。当年,在王铭铭教授的指导下,我译的第一本人类学作品是格尔兹的《尼加拉》,第二本书便是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