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消失掉的东西,构成了一座真实的深圳


制鞋厂女工。图源网络
“每年北京都在说过年的时候很难,因为大家都回去了,但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深圳,深圳基本是空城。”3月28日,著名作家邓一光的“深圳故事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发布会上,邓一光与著名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青年评论家李壮,探讨了有关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学的话题。

十年前,深圳龙华还是厂房林立、布局混乱、尘土飞扬的城乡结合部,如今却摇身变为“深圳北中心”,这部以“龙华”为主题的小说集,用12个故事切片透视城市,著名评论家潘凯雄认为,作品从小小的切口展示了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邓一光是类似于奈保尔的作家,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文学是用感性的、用生活表层的东西试图揭示生活最深层的东西,只有细节才能书写历史。”评论家李壮认为,邓一光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精髓。
以下为发布会对谈速记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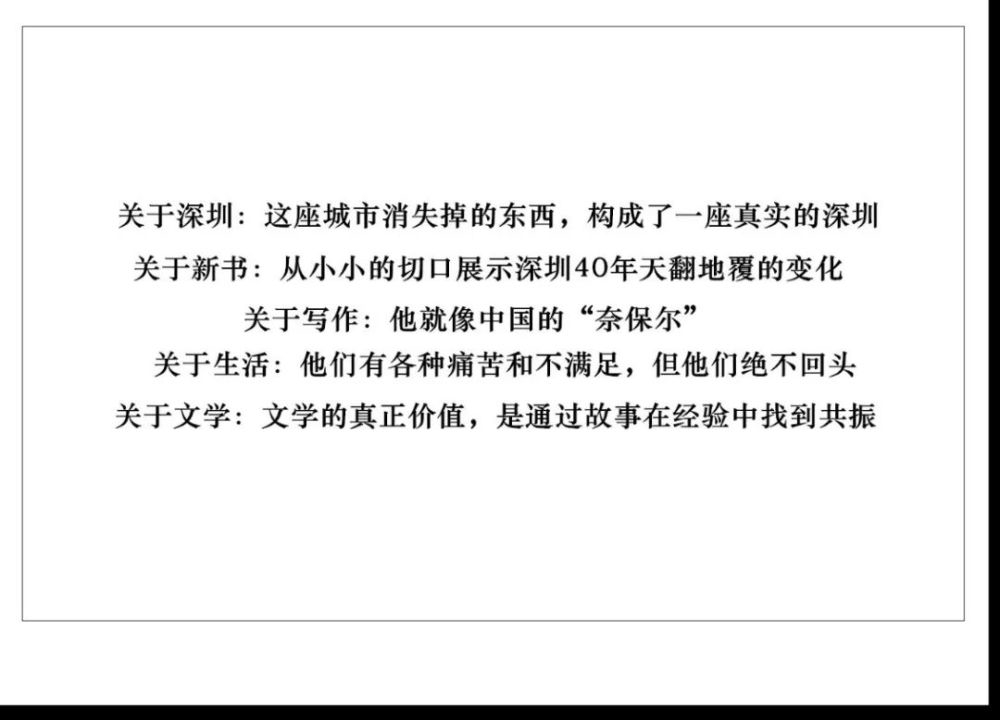
关于深圳:
这座城市消失掉的东西,构成了一座真实的深圳
邓一光:深圳这座城市只有40年历史,过去叫宝安,或者叫新安、惠州,过去也是南江重要的陆海的一个管理地方,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深圳有多重要。我们从建国之后曾经被闭关,和海外的联系是通过香港的,就是通过深圳的罗湖口岸,当时它是一个镇,像一个大村子,它那个地方有海关。二十七点几米的一个铁路,曾经两度,一个是抗战,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和海外沟通的咽喉要道,我们需要的一些资金、一些重要的材料,都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所以深圳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梦做了一百多年,但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这才是若干人的命运,从8亿、10亿、12亿、14亿人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中国人才是真正的成为全球人。从哪开始的?从深圳开始的。因为最早的是珠海、汕头,但这两个没成功,深圳成功了,因为改革开放不是必然成功的,深圳成功了。深圳原有的居民,我们讲的深圳是包括宝安在内33万人,但是原住民只有17万,因为它有很多海关、仓储、国家干部、两个边防团,还有很多警察,所有加起来,原住民只有17万人。现在是2200万人,户籍人口近600万,你想这17万人在哪儿?而且这里有故事,我的很多小说里面都写过,说这些人身价几千万,你不能说,你作为原住民家里有几千万,你肯定出了问题,严格说是每年分红几千万,有一半人从深圳消失了,但是有一部分他们的二代回来了,有些人从英国、美国读书之后回来做投资。而深圳形成资本运作之后,深圳人本身不厉害了,反而是潮汕,像这样的巨大资本进入在做这个。你到一个城市做观察的时候,经济当然要观察,但是最重要的是观察这座城市消失掉的那些东西,他们构成了一座真实的深圳。而这些人要找什么?所谓家是要找什么?所谓家不是要找房子和户籍,他是要找同理心,这座城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找到共同价值、取向,我们同情的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我们主张的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这些东西都要落实在情感上。我们讲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最重要的是,你的情感在一个环境中根本不可信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他们两个相爱走到一起,但问题是在不保护或者不维护,或者在一个情感处于危险、被蔑视的环境中间,你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就出现了,换句话说,那就不是你的爱人,不是你的情侣,那也不是你的一份情感,更谈不上家了。

著名作家邓一光
最早的时候,我去过一个著名企业富士康,富士康到内地之前最早落地深圳,富士康在深圳的这个企业有几十万员工,它的中央食堂是花人民币十亿打造出来的,每次他们是分时间段做上下班的,上下班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看到上下班的时候地皮在抖动,几万人进、几万人出,在那样一个工业化的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面消失掉自己,他们如果要找回自己的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要找回情感,这个故事是讲在都市化进程中间,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
所以在龙华广场跳舞的时候我也去看了,非常惊心动魄。我们现在讲“中国大妈”,其实真正有一个现象大家没有看到,在几十万人的一个工厂里面,有多少人怎么在跳舞、怎么在动,怎么把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制式化的工作之后来宣泄年轻人的能量,以及可能自己的苦闷,甚至未来的希望。这是惊心动魄的,中国像这样的几十万人的大企业几十、上百个。
我们从一个文明形态进入另一个文明形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很多人是从乡村,从村镇,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个大工业的城市里面,我们原来支持自己的成套的文化系统,比如道德、价值观、血缘,这些东西不在了,不在以后什么东西维系自己在生活、工作打拼、人际关系、追求未来生活的过程中给自己以支持?我们还是需要伦理,还是需要价值观,需要认知,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我能做、什么东西我不能做,我向往什么、阻止什么。但是在一个大工业的环境下,尤其是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个重大的转型,从一个封闭的大陆走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个人也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原来的原则不在了,我们要建立新的原则,但是新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故事没有给,它没有原则,因为来不及建立,尤其是作为个体建立原则更为困难。

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潘凯雄
潘凯雄:我们现在知道的深圳,去年总书记去深圳特区40周年的纪念会。我看今天在座年轻的读者比较多,现在大家提起深圳就是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在深圳占有相当的比重,现在的总部经济,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实际上它是在四十年代的历程当中,由一个叫宝安的几万人的小渔村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而来的。在这四十年的历程当中,由一个当时叫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到现在中国现代化都市建设的示范,过去是在这里试验,现在是在全国,某种意义上发挥着引领作用,这样一个历程,由一个小渔村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历程。在这个现代化历程当中,可能现在大家只看到这个城市,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光鲜的一面,或者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这当然很重要,这是深圳发展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当年3万人的小渔村现在发展到2200万人,北京大概3000万,(1000万户籍人口,1000万流动人口,1000万频繁进出的人口),那么一个弹丸之地2200万人口,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而这12个中短篇还是在他们创业阶段,我自己感觉还是在深圳前十年左右或者前十五年左右最基层打拼的这些人,他们的一种生活、心理、精神状态。实际上在深圳四十年的建设发展中,这一批新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重要,当然他们也经历了非常艰苦、非常曲折、非常忐忑的心理历程。
关于新作:
从小小的切口展示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
潘凯雄:这部集子虽然只是12个场景,虽然只是12个切片,但是我觉得把深圳创业时期的那些最底层的新移民的艰苦、心理的煎熬,其实那些新移民好多也是从欠发达地区过去的,他们心理的转变、心理的历程,被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当然12个作品有12个视角,这是整个书的一个大的轮廓,要说大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从小小的切口展示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从内容角度来说的一个特点。
另外从形式上来说,当然我这种概括不一定对,但是主要大概是这样。所谓最会写军人的作家,他表现军人题材的大概都是长篇,至少重要作品是长篇,最有影响的是长篇,而且越来越长,大量引用文献。这些短篇,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汉正街》也好,还是这一本,尤其这一本,第一部你说是中篇也可以,说是短篇也勉强,完整是4万字的样子,但是我觉得非常精彩,最短的才7000字,把一个人物或者两个人物惟妙惟肖的表达出来,而且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我相信在读者心里面,在读者的脑子里,一定呈现的是大场面、大背景,所谓以小见大,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文坛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现在从网络文学来说起手就是几百万字,动辄千百万字也是可能的,但是在传统文学领域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尤其是以前必须通过报刊、书籍出版公开的时候,短篇、中篇、长篇,这个人写完长篇以后基本上奠定了他一个优秀作家的地位,于是乎很少写短篇。所以我们现在短篇小说写得好的作家其实不多的,刘庆邦算一个,所谓短篇小说王了。
一光这个中短篇,尤其这12个短篇都是很精彩的,其实在几千字、一两万字里面,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面,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个大的世界,能够给大家呈现出一个人的丰富内心和灵魂,其实是功夫,这个功夫绝不压于一部长篇小说。世界文学的很多名家,包括欧亨利、契诃夫,是世界著名的大作家都没有写过长篇,都是短篇,当然契诃夫还有戏剧。所以从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来说,而且现在出版社也很少出小说集,这就很奇怪,所以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他的小说集也是特别有魄力的一个作为。所以不管是作者也好,还是出版社也好,在这短篇小说关注这一点上,对文学、对出版、对读者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写作:
他就像中国的“奈保尔”
孟繁华:我觉得一光是特别类似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
一光是2009年到的深圳,到今年已经12年了,他曾经励志要写100部反映深圳生活的短篇小说,现在已经快60部了,一光对深圳生活的反映用短篇小说的形式,他是发了力的。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阐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光的短篇小说,今天谈的是《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不一样,长篇基本写军人的,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到深圳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基本是写深圳生活的,按说他到深圳的时间并不长,他不是土著,当然深圳的土著很少,它就是一个中国地地道道最大的移民城市,而且是中国最年轻的明星城市,我们讲北、上、广、深,它和北京、上海、广州已经齐名,但深圳的历史仅仅有四十年,我看过一些文章,深圳(当时叫宝安)的历史可以到近代,当然我们不是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专家,我们也不能轻易去谈论它,但是这四十年的历史是真实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如何表达深圳四十年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看深圳四十年整个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讲述深圳四十年辉煌历史,这是一种表述方式。我们在其他的艺术作品里面,深圳是一个创作歌曲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比如像《春天的故事》,红色主旋律的歌曲在全国非常有影响。

著名评论家孟繁华
深圳文学的复杂性用“打工文学”来描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深圳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打工文学”概念里面难以涵盖,邓一光就是典型的例子,我曾经给他写过长篇的评论,《深圳在北纬 22°27′- 22°52′》,这两个作品都是反映深圳生活的一个序列,一个作家在写什么就是他在关注什么,也就是说他在关注深圳四十年历史的时候,和其他的历史讲述方式并不完全一样,他的写作,如果按照过去既定的概念也可以称作是底层写作,他写的都是底层,包括《深圳在北纬 22°27′- 22°52′》,包括《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写的基本都是底层人,也就是说大量的深圳移民,移民到了深圳之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这个群体过去叫做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地位非常崇高,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产业化的调整,计划经济的转型,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基本也不提了,不提不等于不存在,比如打工文学本身就是带有阶级属性,这个阶级属性劳资问题。深圳很多作家也都在写这个群体,但写这个群体,他们的写作方式不一样。
一光的写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有非常鲜明的先锋色彩,一个作家受没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这个作家的创作,包括他的修辞,包括他的小说结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李雷讲这两个原则是什么,一光说没有原则,具体说有原则,这个原则是似是而非的原则,是无关痛痒的原则,本质上说它不是什么原则,说跳舞的女孩子衣领别弄太低,第一个扣不要解开,这叫什么原则?这不是原则。底层工人,FC工厂,穿着三色的T恤,红色、蓝色和白色,这是打工族的大军,下班之后像潮水般的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上班、下班,我们看不到的是他们内心的感受,他那种现实生活的存在感和精神状况我们是看不到的。到了龙华跳舞的这个广场上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种宣泄,那是一天的压抑,一天的苦痛在龙华广场上宣泄出来。这里要什么原则呢?这没有原则。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另外一方面,特别是底层打工者,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不承认这一点,我觉得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邓一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比如说写年轻的情侣,他经常写到年轻情侣,包括《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里面也是两个年轻情侣,甚至写到博士硕士的年轻情侣买房子,比如春节过年回家,一票难求的时候,写一对年轻人和家里的关系,都是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这个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他里面也有批判。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表达出来。

老照片,图源网络
关于生活: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苦痛,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他们绝不回头
孟繁华:文学作品不是一个理性的表达,它和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理论、美誉原理不一样,他要用感性的、用生活表层的东西试图揭示生活最深层的东西,只有细节才能书写历史。如果只用一些概念表达历史的话,这个历史是虚空的,各种各样的概念都会生造。生活细节生造出来的吗?细节是不能编造的。情节可以虚构,细节一定要真实。在这一点上一光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原则也好,我们的价值观也好,现在正处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这种明星城市,它城市文化还没有构建起来,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原乡记忆来到深圳这座明星城市,各种各样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多种不同可能正在逐渐构建出一种深圳的文化来,但这种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之所以不发达,包括现在写北京、上海、广州的,写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它和纽约、伦敦、布拉格、彼得堡这些城市不一样,这些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城市文化,通过几百年的发展这个城市文化构建起来。深圳只有四十年的历史,或者中国改革开放才有四十年的历史,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文化经验变成我们的文化遗产,它在当下的生活里不具有支配性,新的构成支配性的文化正在建立当中。
所以每个人充满了迷盲、困惑和我们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密切相关。这种迷盲、困惑和它的复杂性,在一光这12个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北京、上海、广州也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书写这些城市的小说,虽然跟深圳的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那里面充满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承受,现代性不是最好的,但是比较当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现代,难道我们退回去吗?我现在对很多书写乡村,写村里那点事的作品,我看了之后就头疼,村里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回去?那个是回不去的,乡村生活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美学是乡村文化构建的,田园牧歌、袅袅炊烟、纯朴的生活、小河流水,这是乡村美学,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现代,进入现代之后还用乡村构建出来的美学来描述和体会我们的当下,这是匹配的吗?这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讲很多乡愁、原乡,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头,我们别无选择。邓一光在这个小说里面所表达的这些生活细节和情节,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苦痛,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他们绝不回去。

青年评论家李壮
李壮:城市生活看上去很便利,它延续着我们从人文主义以来的让人活着更舒适的文化传统,但事实上,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不是我活着,而是我在城市活着,我以城市的形态活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运转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里面一个齿轮。但跟齿轮不一样的是,齿轮没有思想,我们有思想,我们知道自己被迫运转。这种状态在哪里最集中?可能就是邓老师写到的深圳,这样高度精密化的运转,工厂,那种高速度奔跑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里面这种体验尤其突出。如果我们今天写城市,刚才孟老一直在谈城市问题,如果写不到这种感受,写不到这种非常奇异的他者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书写是不成功的。
尤其我看到这个书的背面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巴黎漫游者》,我特意看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写到十九世纪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那个时代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游荡者,甚至密谋者,他在都市的人群中,他在巴黎的古廊街下面,他感受到的是兴奋和震惊,他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的安放,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一两百年过去,到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在邓老师的书里同样都是漫游者、密谋者、游荡者,但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是在邓老师书里经常写到的。而且他站在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不是人群中的安全感,他反而感受自己的凸显,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尤其在深圳这样的前沿的、极端性代表了今天社会运转的城市里,邓老师写出这种感受,能写出这种感觉的作家在今天并不多。
与之相关的是城市里面的人,第二点就是人。在这里面的人,他出现了异化和失语。当然“异化”已经被用坏了,我谈谈这里面的失语,人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邓老师一开场的时候提到对生活的找回,对精神的找回,在今天非常重要,但是它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你不用说富士康这些工厂里面的人找回生活、找回自己的精神不容易,我找回自己的生活和精神都很难,每个人都很难。
关于文学:
文学的真正价值,是通过故事在经验中找到共振
邓一光:我是去了几个月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去到一个中学。深圳有两个中学有合唱团,因为他们要做素质教育,成立合唱团。这两个合唱团都非常有名,在国际上拿过很多奖。但最重要的是,深圳的教育,父母都知道深圳这座城市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故乡,可能也不是我们的未来,因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到底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同理心,如果没有的话,你在这个成事不可能把它当成家乡。所以教育也是这样,完成孩子的素质化教育,为国外欧洲各个大学培养这样的学生,家长也是这样,教育体制也是这样。
在这里有一个合唱团,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去的,这个合唱团的指挥非常有名,当然现在已经退了,他到最后一课的时候,这些合唱团的孩子进来,因为他们可以最后一堂课不上课,我在排练厅后面看。这个合唱团全是女孩,所以为什么写女孩。孩子进来的时候全部是苍白的、麻木的、没有表情的、疲惫的进来,但是当音乐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细节,我前面都是孩子,在我侧边有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突然把手伸出去,老师说大家注意,我们先把头四个小节唱一下。指挥棒拿起来,这个女孩手伸出来,但是旁边的两个人根本没有感觉手马上伸出来,身子一下站直了,我当时就觉得有另外一种东西在。所谓有另外一种东西,不是只有一个,是在这些生命中间有某些东西值得被我们关注的,生命不仅仅是你的疲惫、你的妥协、你的悲观、你的灰色,还有一种东西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中间你还有什么能量,或者你想做什么。所以为什么写了一个有理想的女孩,但是她其实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比如她想做歌星,你一听就觉得不行。
我这里写到一个细节,这个老师讲非洲的一个音乐家做了关于自然的音乐,这是当时在现场的一个真事,我后来找到这个指挥,把这段拿回来听,但是我本人不是很喜欢,但是我知道就是这段音乐让所有的孩子们从制式化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们可以在这个音乐中找到自己,比如她想哭、她想笑、她想撒娇,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这是当时的一段经历。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两年之后,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摇摇晃晃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要写这个故事。
短篇这种东西命运感很强,当然我不代表别人的经验,我个人经验是你不能拿理性处理短篇。长篇缺了理性不行,但是你写作的时候必须要从那个上面退出来,你的理性有多强可能就有多失败。但是长篇必须是你具有自觉的理性精神,你才有可能去做好长篇。否则的话你堆的就是字数,我们现在大量的就是在堆经验,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短篇不是,为什么说我的短篇风格不确定,就是取决于我当时这个人生病没有、我兴奋不兴奋、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我接触这件事情想表达的时候是灰色的还是明亮的等等,甚至我当时喝了酒没有、吃了药没有,这些都有关系。文学这种事情给我们能够留下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们读了一个故事,而是我通过这个故事在我的经验中能不能找到共振,甚至修正我对生活生命的一个看法,这是必须要有某些东西存在的。长篇首先是结构,不是经历。很多人经历特别好,你拿出来以后很快就没了,我们都承认这个故事非常好,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在传统文明和未来文明中间找到一种方式,我们的时间轴怎么加上去?没有,你必须要有结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