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审视2012年公安题材小说
 2021-03-27
2021-03-27

尽管“公安题材小说”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学院派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认可,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类的本本中也很难觅到这一专业术语,但我坚持言说之。正如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过去的2012年,十多篇(部)公安题材小说给我印象很深,现耙梳一番,以飨读者。蒋子丹的《囚界无边》(《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3期)、张廷波的《冰吻 红唇迷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3月版)和吕铮的《赎罪无门》(《当代》第3期)三部长篇小说较为厚重,对人物一波三折的命运揭示得较为深刻。其他中短篇小说之所以过目不忘,自然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通过细读,发现这些公安题材小说与以往的同类文本相比,具有如下优势和特点:
隐喻性强
近些年来,公安题材小说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表现中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内在的精神表达,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精致细腻,表达的层面也越来越丰富。且看《囚界无边》这一小说题目就富有隐喻意味。文本讲述的是看守所这个“囚界”里发生的故事,并借地震这个突发事件来挖掘人性深处的隐秘。在那高墙之内,各色人等真相毕现,为读者展示了一幅鲜遇少见的人生图景,尽情地凸显了人性之美。其深层意义是说无论何种职业、何种年龄、何种身份、何种地位的人总是被“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操控着,遭遇着太多的不确定性,隐喻之意是人的生存境遇本来就是一种“囚界”。胡雪梅的中篇小说《麦香》(《啄木鸟》第12期)这个题目也是如此,麦香原意是指麦子很香,实则隐喻警察老吴与何枝子在麦地里产生的纯洁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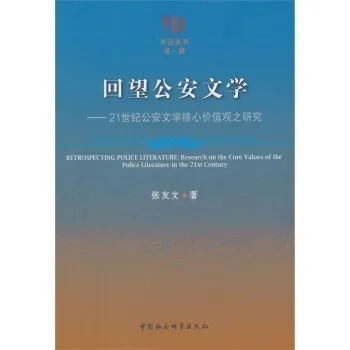
美国当代著名的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认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即必须依赖隐喻和象征来完成“意义”的传达。张策的中篇小说《新闻发言人5》(《啄木鸟》第5期)中的新闻发言人李涧峰在高速公路收费站等待交费时想:其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个人啊,一生的转折不一定自己都明白缘由的,有时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这样了。就像这条路,谁知道啥时候哪个岔路口蹿出辆车来,也许就剐蹭了,就撞车了,人的行程就改变了。紧接着叙述自己的同学如何官运亨通。作者分明是在用高速公路来隐喻人生,抑或人之命运。文中还出现了两家洋快餐店纷纷发传单、竞相打广告的场景,标志着一场争夺客户的战争已经打响,同时也喻示着官场博弈的激烈与残酷。
魏人的中篇小说《新龙年警官》(《作品与争鸣》第7期)中品茶那一段情节饶有意味。仔细品味傅冬与马局的对话,话中有话,弦外有音——都没说破。譬如“马局拿起水壶给傅冬续上水,‘ 这我知道,你也知道。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傅冬喝了口茶,‘现在这茶酽了,有苦味了。师哥,有些话可以点到为止’。”字面意思是说茶的味道有变,隐含之意是说这案子日益复杂。傅冬和马局当时是在拿张玉贵说事,说他与当事人唐敬容曾经是战友。如果继续让张玉贵侦办此案,似乎有些不妥,有必要让他回避。等到张玉贵和马局在一起喝茶时,马局依然重复着续水的动作,表面上也是在品茶,内里却是在说工作、谈人生。马局实则是在借喝茶的机会告诫或提醒张玉贵什么的,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陈世旭的中篇小说《一看就是个新警察2》(《小说选刊》第10期)中借一段高档楼盘的售楼广告词——“你将拥有的居所,常人要用一生去想象”道出常人与非常人的区别,意味隽永,有嚼头,有品头。作者先把某国总统比作非常人,然后再把副局长刘国宝和铁头放在一起作比较,谁是常人,谁是非常人便昭然若揭。那个总统的“亲民”之举不正是铁头对刘国宝“谅解”的隐喻么?
《冰吻 红唇迷影》中隐喻多多,氛围营造步步到位。就拿儿子回家对父亲说起涉及副省长这个案子来说,父亲并没有明确地答复儿子如何应对,而是与儿子推沙狐球,并鼓励他:“记住,就像推沙狐球,只要有一次推球机会,就有了一线希望。”这一处隐喻形象贴切。父亲虽然说得不甚明朗,儿子却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打开案件的缺口,而“副省长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是要破产的”这一迷信说法则是副省长的命运之魅,并为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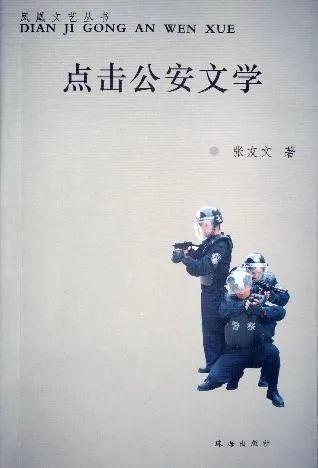
何顿的中篇小说《青山绿水》(《花城》第4期)具有很强的现实隐喻性。何为“青山绿水”呢?何顿说:“小说取名《青山绿水》,是有寓意的,至于是什么寓意,我不说,怕误导读者。人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思想、智慧,对任何事情的理解都是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思维,我说出我的思考,不见得你会认同,所以我引而不发,憋着,让不同的读者寻找不同的答案吧。”小说中有两处“青山绿水”,一如人民警察黄志来到杨小玉家,发现了一块好住处:“从堂屋门望出去,青山绿水的,就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好像生活在另一个平缓、安宁、友爱的世界一样。”又如黄志被调动到偏远的驼峰山派出所之后,面对疯狂盗取林木的盗贼,“我想再不开枪我命都会丢在这片旖旎却凄凉的青山绿水中腐烂。”前一处“青山绿水”是世外桃源的隐喻,也是杨小玉精神世界的写照,后者则具有反讽意味。
李辉的中篇小说《游戏规则》(《北方文学》第4期)通过“我”来看“公安”,看公安机关里的福利待遇,微妙的人际关系等,实则是官僚政治的隐喻,有卡夫卡的《城堡》之味,相异之处是前者进了“城堡”而后出来,而后者是始终没进入“城堡”。
由此可见,隐喻性的修辞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文学性,也使得文本的意义具有阐释的多种可能性,理所当然会在不同读者大脑中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赫伯特·里德说:“隐喻则是把对事物的多方面观察综合为一个主导意象;它表达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不是用分析,也不是用直接陈述的方式,而是凭借对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的骤然领会。”(《英语的散文风格》)“青山绿水”“游戏规则”等主导意象蕴含了无法用理性方式分析和表达的思想,恰好印证了“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这一理论。米兰·昆德拉说:“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隐喻的作用不可小视。
震颤效果
美国的爱伦 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对读者感染的程度。
孙明华的中篇小说《情非得已》(《啄木鸟》第2期)中的人民警察余小伟本是一个伟丈夫,也是一个好丈夫,却不招妻子苏婵儿待见。他在外面尽职尽责,细心查找案件的蛛丝马迹,结果却发现妻子苏婵儿出轨了,“对于余小伟来说,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天塌地陷、雷鸣闪电般地把他的心轰炸得四分五裂。”苏婵儿出轨不仅震惊了其丈夫余小伟,同时也震惊读者。
《新龙年警官》中的张玉贵面对昔日的战友,又遇分别二十多年的妻子,内心本已波浪滔天。随着情节的推进,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竟是他负责看管的污点证人、一个钢管舞女郎、一个特大贩毒案件的嫌疑人!生活真是一个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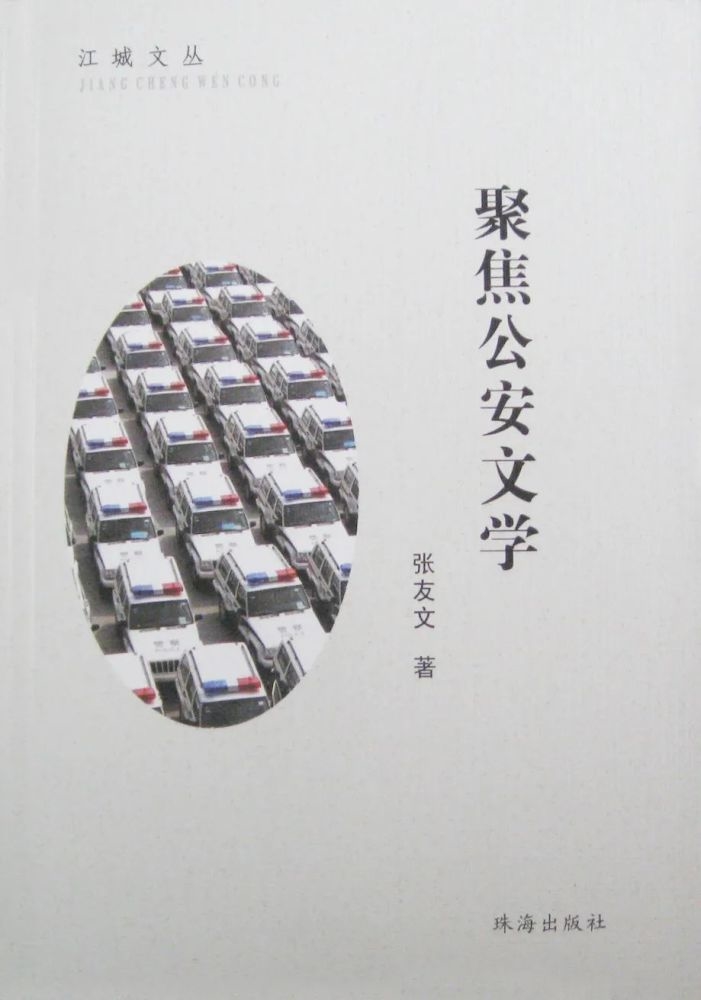
《赎罪无门》中“两个脖子已入土”的主人公内心较量“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人民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三两句道不明、说不清。追溯至案发之初,才发现真的是震憾人心。固执、要强的警察老马即将退休时发现了一个有疑问的卷宗,顺藤摸瓜牵出了诸多刻骨铭心的往事。扣人心扉之处是老马即使身患绝症,却矢志不移,忠心不变,排除万难弄清案件真相。老马的确堪称精神英雄,似瑞士迪伦马特《诺言》中的马泰依,也似张策《无悔追踪》中的老肖。
《麦香》讲述的是“田埂子警察”老吴到北京寻找爱情的故事。小说相当篇幅是在描写老吴与何枝子之间过往的真爱,诸如老吴给被害人家挑水、做小工、说好话达十年之久,旨在乞求他们原谅何枝子,为他早日归劝何枝子投案打下基础。欲上北京前,老吴准备充分,给心上人买了好多好多她喜欢的东西。前往北京的路上,老吴时常梦见思念已久的爱人。可是,千里迢迢,历经千辛万苦,结果让他,也让读者心碎、心颤。原来朝思暮想的梦中美人早已化作尘土,老吴抚摸着何枝子的墓碑,泪如雨下,我们读者又怎能不为之动容?
张驰的短篇小说《看守所》(《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第6期)是一个关于人生充满悖论的故事,充满批判现实的力度。小说刚开始就用了反讽的口吻,譬如“黔首市白石沟看守所前所长孙青亮是在火车站被执行强制措施的。”带着好奇一路读下去,才发现孙青亮原打算调离这个偏远、枯燥的看守所。通过四处打听、活动,好不容易高攀上了省厅监所管理处吴处长。吴处长向他许诺机会成熟就给他挪个地方。孙便寄希望于吴,不时地进贡什么的,当然也要为他办事。在孙的职责范围之内,曾为吴“帮忙办一个留所服刑”。慢慢地“孙青亮与吴处长进入了良性互动的阶段,在很多上了台面的场合,吴处长对孙青亮开始称兄道弟,称他为基层的小兄弟。省厅的吴处长都在公开场合与他称兄道弟,市局的一些狗脸也就跟着变了,开始对他绽开了讨好的笑容。孙青亮的沮丧感渐渐灰飞烟灭,觉得重树了人生的自信。”孙开始觉得日子飞扬起来了,看来离开看守所的日子不远了。后来孙帮吴帮得太离谱,竟然办了不符合规定的保外就医。那个被保释的家伙又犯了重案,“孙青亮被投入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白石沟看守所。”等到孙青亮刑满释放时,他才真正地离开了看守所。当然,像这样的离开,并非他所愿。
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艺术性,之所以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就是因为在艺术形象中渗透着作者强烈而真挚的思想感情。上述作品已不再遵循传统的叙事美学,部分细节或情节或故事完全打破了平和的、静态的审美观,与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大相径庭。究其实质,还是为了制造“一种效果”,加大文本对读者感染性的力度,充分地彰显文学的感召功能。
伊塞尔认为,文本是一个充满各种潜在因素因而有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加以具体化的结构。不同读者在细读上述文本时所获得审美感受会有所区别,而且在不同心境和处境中所获得的震颤效果会大不一样。公安题材小说堪称涉警题材,直面生死和情感跌宕的情节、场景自然比非涉警题材文本多一些。2012年公安题材小说与往年相比,不再用浮泛的呐喊企图制造做作、痉挛的效果,而是在氛围的营造、情节的巧合、人生的悖论等方面下足工夫,让读者从中读出共鸣。
心理刻画
丹麦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012年的公安题材小说中相当篇什倾向于心理展露,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堪称入木三分。
孙明华的中篇小说《情非得已》(《啄木鸟》第2期)令我格外着迷之处在于其细腻的心理刻画。警察余小伟的妻子苏婵儿为什么会出轨?其心理流程可以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来解读。荣格所说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两种重要原型,前者系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而后者是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至于苏婵儿心中的阿尼姆斯,叶闪一针见血,她对余小伟说:“我知道她(苏婵儿)为什么这么做,是想做给你看,她比你做警察的要英勇。她跟赵四交往并非爱他,也并非不爱你,她是觉得你当时太窝囊,尤其是网络和报纸等媒体对你的行为进行质疑的时候,她宁愿看到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堂堂正正死去的烈士,也不愿意看到你在夹缝中苟且地活着。英雄梦破灭后,那段时间我想她一定很痛苦,却又无法对你讲,你想连你妻子都不能理解,普通群众为什么要理解一个警察呢?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爱勾引女人又爱逞英雄的赵四。她把赵四的‘英雄主义’化作了对你‘懦弱’的报复,她把对赵四的爱转化成对你以前的爱。”苏婵儿心中的阿尼姆斯应该是刺刀见血的勇武形象,因此,她就不能理解丈夫余小伟的隐忍之大勇。

孙学军的短篇小说《傍晚的阳光》(《啄木鸟》第8期)这一题目从象征层面来理解,源自于唐朝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在外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桑辰得知儿子“宇生出息成大小伙子了,这足以让他这个当父亲的在内心里感到骄傲。”妻子春枝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如此幸福的场景却不能久长,因为他要去自首,“清网行动”已逼得他寝食难安。小说把桑辰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一个人孤身在外,不时地思亲想家,愧做父亲与丈夫,特别是愧对昔日朋友罗成一家。“这么多年,他没间断过给罗成家寄钱,就在他最难的时候也从牙缝里省出点钱往他家寄,那一次最少,只有十块钱。桑辰清楚,拿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罗成的命,在法律上也赎不回自己的罪过。他只是要找一些安慰,在心里上的。”从文字层面看,桑辰的忏悔、赎罪心理不言而喻。忏悔实质上是良知意义的自我审判。桑辰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的心态各不一样,或焦虑或紧张或害怕,但“悔恨”这一核心字眼一直像梦魇一样缠着他,可谓真实精到。在孙学军无情的解剖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桑辰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看到他那恐惧、孤独、矛盾,乃至分裂的内心世界。前文所述的《赎罪无门》也富含忏悔意识。自从张鹰死后,张文昊和老马的良心一直不安。
《青山绿水》中的人民警察黄志竟亲手把叔叔——大恩人给枪杀了、把这棵大树给放倒了。走笔至此,作者才开始着笔这个人物“受难的灵魂”和内心的“搏战”(胡风语)。流言四起时,“一个说我喜欢上了只比我大两岁的婶婶,趁着这个机会一枪击毙了叔叔。另一个版本说得更离谱,说我和婶婶合起来贪叔叔的财,那个电视台的男人是我和婶婶做的套。还有一个版本说得也没边,说我大义灭亲是为了升官发财。街上的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是的,恩人被自己置于死地、后台被自己撂倒,黄志本来就良心不安、痛楚万分,而流言蜚语又如雪上加霜,可谓万箭穿心。这是非同一般的内心煎熬,只有身为人民警察的他才能深切地体会并默默地承受。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详细地描绘黄志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黄志本人也没有道出,读者只能凭借想象得之。这些空白的存在使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动力性和开放性,文学性大增。通过读者的想象也使人物的心理更加丰富,文本虽未有意刻画心理,却胜似刻画。
邓宏顺的中篇小说《归案》(《湖南文学》第11期)中虽然内心活动笔墨不多,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却很大。警察陈副大队长在良心的驱使下帮助嫌疑人李泽洲讨工钱,“以心换心”,李泽洲的灵魂也复苏了,但其心理转变的详细过程却省略了。他说:“我不愿做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否则押解途中可能有意外发生,据说“他们(李泽洲夫妻)已经悄悄商量过了,如果不让讨工钱或者讨不来工钱,他们就在路途上跳车逃跑或者一起寻短。”由此可见,顺利押解还得益于陈副大长深谙犯罪分子的心理,他说“这个嫌疑犯不同于一般嫌疑犯,这笔血汗钱没有收回来,会是他最伤心的事情,他甚至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都有可能。”
上述文本通过幻觉、梦魇等情景的描写,使心理刻画更加真实,彰显了各类文本的艺术特色。实际上,复杂的情感纠葛在《新闻发言人5》《新龙年警官》等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毕竟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文学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很大程度上以情致胜。而“情”多半是读者从人物的心理世界获悉的,这也使得心理刻画在文本中尤为重要。
又及其他
走笔至此,意犹未尽,还有一篇佳构不得不提,即李永旭的短篇小说《编外神探》(《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第12期)。其独到之处在于大胆地质疑公安系统的用人机制,当然也是对整个当下国家录用人才模式的批判。如今选拔人才的口号是唯才是举,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条条框框太多,有性别、学历、经历、年龄等的限制,有系统内外的差别。解放初期,盗贼都可为“我”所用。为何在民主盛世的今朝,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反倒被埋没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句的生命力犹存。小说主人公杨子是个编外神探,功夫却了得,火眼金睛,得到几任派出所所长的器重和赏识。治安太乱时,所长们想到了他;治安趋好时,所长们请他另谋出路,理由是派出所经费有限,养不起他。是何言,是何言?小说结尾隐喻高妙。神探杨子与小偷到底谁是小偷,好人与坏人怎么区别?言外之意,到底谁是有用之人,到底谁对社会有贡献?这个开放式的结尾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世道真是越发让人捉摸不透了。像杨子这样具备一技之长的高人尚且面临着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何况常人乎!这么说来,还是一篇探索人类困惑主题的文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伽达默尔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永远是相对的,它不可能为作者的意图所穷尽,而总是由阐释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的历史所决定。欲弄清真相者,还是亲自去读《编外神探》较好。

如果围绕“同事情谊”、“人文关怀”、“梦幻叙述”等关键词做文章,上述公安题材小说又有说道。例如文本皆是充满温馨的叙述,不像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写作那样不动情观照,如《新龙年警官》中的甘天娃提醒支队长张玉贵吃早餐;《新闻发言人5》中李涧峰与小陈局长两人之间宝贵的同学情、战友情等等。他们也不像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样支离破碎,都有这么或那么一个“中心”,正如葡萄文学巨匠萨拉马戈说:“我的每一本书都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澄清一个疑问,厘清一种想法,表明我是如何在这个世界存立的,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抑或我是如何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解的。”文学的力量与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在这个浮躁功利的年代,在这个欲望书写流行的当下,2012年公安题材小说大都能滋润读者心田,传递给读者的是信心和温暖。与往年相较,2012年公安题材小说独到之处不再是单声调地颂扬人民警察,而是开始呈现多声调,即对人民警察提出质疑或批判,如《游戏规则》《看守所》《编外神探》即是。
由此可见,公安题材小说的行业性在增强,文学味也在增强,且与公案小说及侦探小说渐行渐远。大体而言,公案小说乃中国本土思想与佛教思辨之合物,而侦探小说则是西方科技思维和司法制度之合品(于洪笙《重新审视侦探小说》)。如今,公案小说和侦探小说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是,公安题材小说坚守的依然是文学性。人们始终都需要文学性,无论哪种文体,哪种媒体,只要其中叙述出了别致独到的人生经验,语言优美,言外有意,话里有话,能够引发读者或观者激动和想象,即其中含有较高程度的文学性(刘俐俐:《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文艺报》2010年3月19日)。
以智慧性著称的侦探小说特征却非常明显,遵行着发案——破案——结案的老路子。它以扣人心弦的悬念、严密精确的推理、剥茧抽丝般的解谜而取胜,包含着巧合、悬念、智慧等共性元素。《情非得已》后半部分就具有非常典型的侦探性质,它突然抛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案子,强化的是悬念冲突。此小说让我刻骨铭心并不是因为其“险奇”美学风格和伦理教化功能,而是其心理发掘的深度,譬如警察余小伟的妻子苏婵儿出轨的心理流程惊人的真实。
综上所述,公安题材小说和侦探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两者有重叠之处,前者突出的是文学性,旁及职业特征,而后者强化的是类型特征,彰显的是惩恶扬善主题。至于文学是否具有职业特征众说纷纭。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多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较强的职业特征,且人物形象身上的职业特征是如此鲜明,以至于让人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这个形象就是这种职业,这种职业就是这个形象。如一说起资本家就想到了《子夜》中的吴荪甫,一说起地主就想到了《高玉宝》中的周春富,一说起农民就想到了《陈奂生进城》中的陈奂生。这些文本的成功之处归功于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自然产生典型化的效果。因此,在信息爆炸化的当下,在生产海量文本的今天,把公安题材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来研究,重在追问其文学性,并顾及其职业特征是可行的。
面对一年无暇统计,也无法统计的公安题材小说,任何一种描述都显得捉襟见肘挂一漏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作品皆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毕竟系涉“警”题材,个别出类拔萃之作可以说取得了不俗的思想艺术成就。我坚信本人的言说均是从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字里行间倾注着在下的一腔热忱,并相信公安题材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自有其看点,有研究的潜质,而且发展前景可观。
(注:此文发表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公安作家》2013年第3期、《新疆公安》2013年第4期、《警官文学》2013年第5期,并收录到《回望公安文学》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