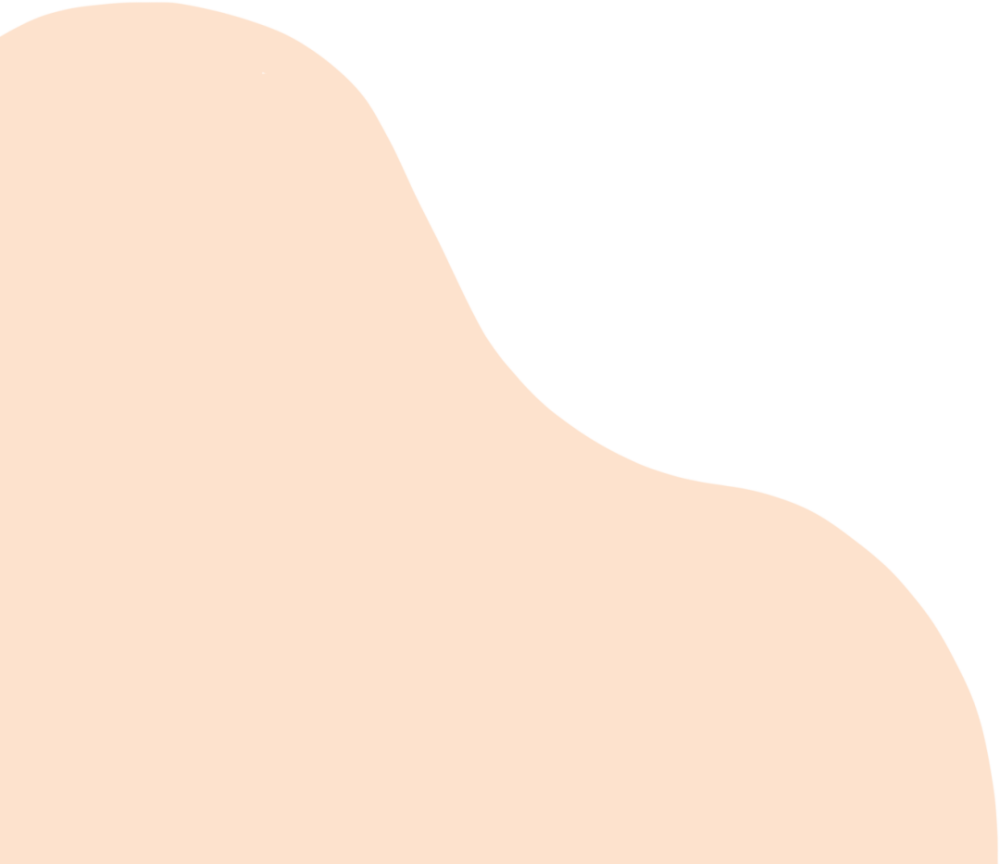做人,重复有重复的意义
 2021-02-19
2021-02-19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
所谓喀戎,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人马”。它们分为——一类是人类的朋友,好莱坞电影中多次出现过;一类是人类的天敌,危害人类没商量,有时完全是出于任性,突发暴怒,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任何原因。不但危害人类,也攻击神族。故宙斯曾告诫诸神:勿招惹彼们,那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曾偶然从画册上见到一幅“人马”的雕塑图片,是罗丹的作品。那“人马”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上身即是人的那部分,向上伸直双臂,挣扎着,痛苦地扭动着,不达目的不罢休地,竭尽全力想要从马也就是兽的下身中脱离出来……
近十几年,每当我叩问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时,总是会联想到罗丹的“人马”。
人类无疑进化了的;不靠文化仅靠科技不能实现进化。往三四百年以前的历史回望过去,结果会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人类才是人类恐怖的天敌;人类对人类的凶残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凶残。任何其他物种都不会仅仅为了取乐而折磨其它物种,更不会自相虐杀、娱乐;人类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乐此不疲。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进化了。
但进化了的人类也就是“成功”地从人马的“下躯”之中脱离出来能以双足站立了的人类,心性就绝不再受“人马”之基因的影响了吗?
有些人做到了。他们可谓是“大写”的人,“纯粹”的人。
有些人仍在向往,所谓“进化尚未成功,自家仍须努力”。
有些人并无再进化的愿望,本质上还是“人马”,并且自适着。但人类的社会毕竟已经特别文明,治理社会的能力一再提高。所以本质上还是“人马”的人渐成少数,且不敢任性地造次了。这是人类进化的成就,使少数“人马”也具有了“后人马”的策略——寻常看不出,偶尔露凶暴。
而我以己眼扫瞄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所见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
我不属于第一类作家。但我也创作过第一类作品,如《恐惧》。正因也创作过,深觉那不能成为己任,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我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我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我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是未得要领。
于是,我的创作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于是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
这样的人是大多数。继续进化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命本能。这种本能的过程非是花蕾开放般的过程,而是自己对抗自己,自我挣扎的痛苦过程;失去的是马蹄和马皮,获得的是人的“全身”。
伪装的马蹄和马皮对于人也依然是有失尊严的;并且伪装而久也属疲劳之事。有痛苦则有深刻。我试图从此种痛苦中窥见深刻。
我之欣慰在于,古今中外,与我抱持同样之文学理念的作家居然不少,作品也比比皆是。我只不过在重复地做他们做过的事。我不因此而羞耻。
重复有重复的意义——为那些正努力从马腹中挣脱出来的人和自己点赞,在我这儿是为意义也。最后,当然也得说说我的新作《我和我的命》——只字不说就等于没完成约稿任务啊!
新作中的人物,如文婉之、李娟、张家贵等,几乎各自都有干脆像“后人马”那么自适地活在人世间的理由,但各自都不甘于那么活着;各自都认为那么活着也活得太没“人样”了。
方婉之们不怕“平凡”地活着,而怕自己会自适于像“后人马”那么活着!我以新作向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同胞致敬!倘他们非是虚构的人物,并且存在于我的“社会关系之和”,我会引以为荣的,也会使我更热爱生活。
在我看来,倒是某些似乎“了不起”得很,“不平凡”得头快触到天了的人,其实本质上只不过是“后人马”,伪装成麒麟皮的马皮之下,包裹的是违背进化论的魂。
小说中,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我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
李敬泽说过,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我愿意迎难而上,保持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对金钱和财富的无止境的贪占心是可耻的;倒是方婉之和李娟们那种平凡而有尊严地生活着的人,在我看来,有着成为优秀“新人”的潜质——起码相对于各自的上一代人是“新人”。
向方婉之学习!
向李娟致敬!

《我和我的命》(节选)
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像我二姐的女儿抱住我那么突然。
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啊!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儿的希望。
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
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
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儿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
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〇〇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三千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给的心也根本没那份给的能力。
我之舍得,是为了断。
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说,怕极了。
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
我想用九千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
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
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点儿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如果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神仙顶的变化就如蜗行,而且体现为各家各户小打小闹的“折腾”。
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
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惶恐。
我怀着此种惶恐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书房,在台灯的光照之下,我养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他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门被我推开那一刻,我宁愿自己是瞎子。
我养父紧跟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
我冲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明天我再向你解释……”
“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
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
“那更可耻!”
“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
他的音调都变了。
他恼羞成怒了。
“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了。
我拒之千里地说:“我要睡了,请离开我的房间行吗?”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掼门而去。
半夜,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年却自认为已没“资格”再当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县一家最好的宾馆。它是养父替玉县融资,请人设计,在二〇〇〇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学,拉杆箱是他给我买的。除了那家宾馆,别的入住之所可能都会有人认出我是谁,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议论。我在玉县的知名度太大了,并随着他的政绩而日增。除了他给我买的拉杆箱,我也再无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冒犯,告诉他我情绪平定了,要直接回学校去了,请他对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对我的态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评。他说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长妈妈”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还是“校长妈妈”和他的证婚人。因为我小孩子不了解的某种“历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长妈妈”生前经常当着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边,你可要替我照顾他。”
养父的解释听起来像小说情节。
我说:“爸,你们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令我感动,我再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他听出了我并不怎么相信,又加重语气说:“你‘校长妈妈’也给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遗书,你再回来我可以给你看。你不要因为你的‘校长妈妈’不在了,就觉得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说:“爸,我明白。”
实际上,我确实认为那个令我眷恋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么还会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阿姨已够使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阿姨的三亲六故,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