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的2020书单


《历史学研究》,[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
《历史学研究》,[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
莫米利亚诺无所不知,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令广大学者闻风丧胆的人。
这本书是他1966年出版的论文集,共收录13篇文章,发表于1950-1964年之间。其中既有50多页的专业论文,也有20多页的前代著名历史学家的学案。最硬核的是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考察《罗马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的真伪以及公元6世纪的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这些硬考据的文章,我们非专业读者远眺即可。如果凑得过近,容易被内力震伤。
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 liano,1908-1987)历来以无可匹敌的渊博著称。他的著作每一页都滴满血淋淋的博学,很多脚注中都埋藏着馈赠给二流学者的学术题目。如果想检测的话,只需看看第一章《古代史与古物学家》中他所引证的那些16和17世纪历史学家中,我们究竟听说过几人。又比如第三章,这是典型的学案式研究,评价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在古希腊通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这篇20多页的文章,如果莫米利亚诺没有通读过19世纪英、法、德、意各国出版的所有重要的希腊史,是无法写成的。而且他对19世纪英国学术的熟悉,让人感觉他刚从卡莱尔和密尔身边穿越回来一般。正是因为这种让人想嫉妒都无从嫉妒的博学,才带来作者下论断时所特有的自信和威严。
第五章写的是俄国著名古代史大家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 Rostovtzeff,1870-1952)。他在1918年之前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后来流亡到欧洲,最终落脚在耶鲁。罗斯托夫采夫据说能用六种语言授课、吵架。因为西方古代史学者通常不会俄语,所以早在流亡之前,他就不得不用德文、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表论文,后来还将自己的俄文著述译成欧洲语言。为了说明苏联学界对罗斯托夫采夫的态度,莫米利亚诺甚至引用了不少俄文文献(中译本第125-126页)。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已足以说明莫米利亚诺的学术触角和语言储备早已伸到普通西方学者难以到达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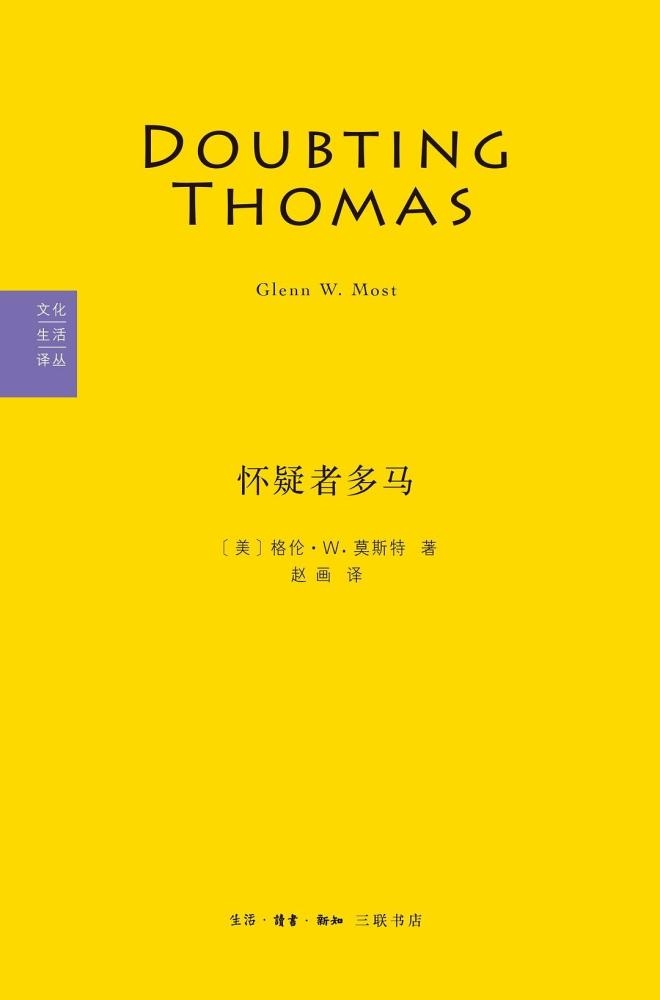
《怀疑者多马》,[美]格伦·W. 莫斯特著,赵画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6月
《怀疑者多马》,[美]格伦·W.莫斯特著,赵画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6月
这是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写出的书。
老话说,眼见为真(seeingis believing)。其他感官(触觉、嗅觉、味觉、听觉)要求我们实在地接触外物、或者摄入外物,而唯独“看”,与外物保持距离,将外物彻底客体化。《约翰福音》第20章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而多马(Thomas)不在现场,所以死活不信。多马非常执拗,非要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不可,也由此获得“怀疑者多马”的称号。结果,多马的师父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八日之后,耶稣向多马显现,让他看、触、探。多马惊呼,怀疑终结。
莫斯特(Glenn Most)针对西方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怀疑主义瞬间,对这则故事的本义、续写/改写、注释和图像呈现(以卡拉瓦乔著名油画为代表),作了扫荡式的历史考察。所以,这本书涉及四个领域:新约、诺斯替派、早期基督教解经学、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艺术史。作者对每个领域的研究都极其深入,所以这本书最能体现莫斯特特有的渊博和跨界。莫斯特教授于2019年访问北大时,曾告诉我这本书的标题原本拟作Believing Thomas(《起信者多马》)。但哈佛大学出版社坚持Doubting Thomas这一传统说法,结果书的销量还颇好。
我之所以说这是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写出的书,是因为莫斯特在耶鲁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还在图宾根大学获得古典语文学的博士学位。他是当前古典学的顶尖学者,而且就像伯希和一样,发表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论文,却基本不写专著。因此,这本书就更显得稀缺而重要。

《吴雷川日记》,吴雷川著,李广超整理,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吴雷川日记》,吴雷川著,李广超整理,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吴雷川(1870-1944)是燕京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29-1933年),是中国本土派神学家。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年),近年来有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但其他著作(比如1940年出版的《墨翟与耶稣》)则少有重印。这部最新整理出版的日记,始于1930年,当时吴雷川已到耳顺之年,终于1943年7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所以,更贴切的标题似乎应该是《吴雷川晚年日记》。
这部日记提供了有关吴雷川生平和行事的大量信息。具体来说,日记中保留了一些重要书信,内容既包括谈学论道,也涉及燕大的校务和家事。比如,他致燕京大学校董的请辞信、与张元济的通信就比较重要。特别是1933年他给法学院学生刘海峰的回信,以最简洁的方式概括了吴氏神学的要义(第102-103页)。更有价值的是一些演讲的草稿或者提纲,有些后来扩充为正式文章,刊登于报章之上,也有后来不曾正式发表的讲稿。这些对于考证吴雷川的著述、理解他的思想,都至关重要。比如,在1932年一则日记中,他勾勒了墨子思想与基督教之相通处,尤其指出墨派之组织与后世的政党和教会非常类似。这些观点,未必是他的独创,但对于考察《墨翟与耶稣》一书的写作过程很有帮助。
大部分年份的日记时断时续,只有1942年的日记为最全,长达200多页。吴雷川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燕园的情形,提供了燕京大学校史的一手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面面的历史细节: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等燕大教授在身陷囹圄之后,他们的夫人如何终日商量营救事宜;日本宪兵队的韩国翻译官向吴雷川求字;燕大与日军协商,发放教员的遣散费;吴雷川为生计所迫,出售线装书,日记中有目录和估价;燕大教授被迫搬出燕园,最后整个朗润园只剩吴雷川一家。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今天读起来格外沉痛。
这部书根据《现代日记丛钞》影印本整理,但编辑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研究者在引用时,仍需对照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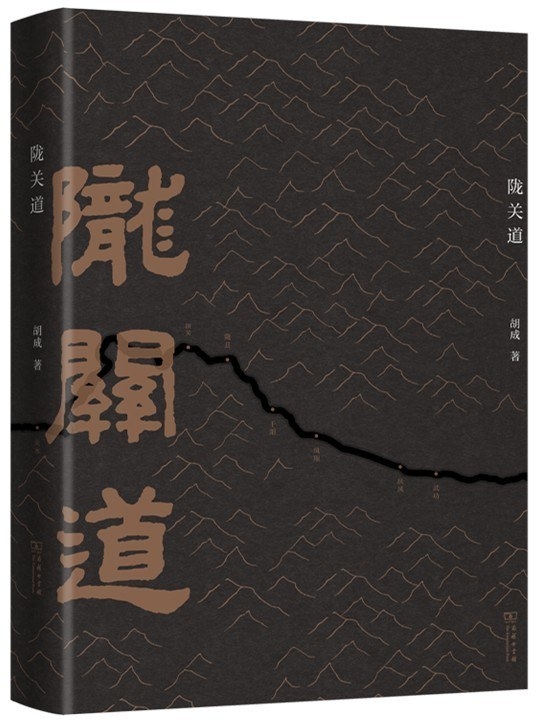
《陇关道》,胡成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陇关道》,胡成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陇关道”,指从西安出发,沿渭水,经过凤翔、秦州,最后到达兰州的这条南道。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一直到唐代,这便是长安往来西域的主干驿道。作者说:“戍边的士卒、出塞的商旅,以至联姻的公主、取经的和尚,皆走此道”(第43页)。说得不能再好了。陇关道的军事、经济、政治和宗教意义都埋在这句话里。
作者就沿着这条古代驿道,参考着陕甘两地的方志、以及清人和民国作者的多种纪行,乘火车、汽车、三轮车,一路西去,观碑访碣,“索隐古人的一些生平、一些心迹”。每到一地,往往先有一段起兴,定好基调,然后就是访博物馆、访古迹、访碑。从古书和碑刻中出来之后,作者就一头扎进市井社会,热气腾腾地描写西安的羊肉泡馍、梆梆肉和陇州的豆花泡馍。残碑断碣和人间烟火穿插融合,让人不禁模糊了古今的分界。
作者语言极其凌厉,有一种碑铭和镂刻的感觉。写历史上的庆寿寺,“漫山神佛,满天花雨”。写谪戍新疆途中的裴景福,“昨日肥鹅,今日古镜”。现在少有人能写这样的中文了。我恋恋不舍地读完《陇关道》,立即把作者其他能买到的书都给买了。
高峰枫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