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温馨的记忆:我与《福建文学》
 2021-01-24
2021-01-24

大王叫我来巡山,听听三刀侃大山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给《福建文艺》投稿,只记得第一次接到《福建文艺》的信是1978年的春天。
白色的信封,红色的地址,浅蓝色的字。
写信的人叫庄东贤。庄东贤的字有些懒散,像一个春困的少女。
庄东贤的信很简单,大意是,你的小说有新意,我们准备刊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整个春天我都在等待。在等待中把信反复看,看出一个大问号:红色的地址是福州杨桥路,而信封上的邮戳表明,这信发自龙岩。
我设想了许多答案,可想得越多,这信越值得怀疑。
想斗胆写信到编辑部问一问,又不好意思。想一找一本《福建文艺》看看,没处找。

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突然有一天,一只白色的信封从报纸上掉下来,我放下正在翻看的报纸,从地上拣起信,心格登跳了一下。
我先看邮戳,这一次是寄自福州。但字迹却是另一个人的,没有署名,署的是编辑部小说组。
信上说,你的小说总体来说是不错的,但要修改一下,请你×月×日到编辑部来。
虽然有些失望,我还是拿着信去向领导请假。领导眉开眼笑,说我们单位出了秀才,当即准了假。
我找到编辑部时有些失落感,在我的想象中,编辑部不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我说不清。
但不是这样:几间教室一样的大房间,桌子的摆法与中医门诊部不相上下。桌上推着一叠稿子,显得很乱,很暗。

我手里拿着编辑部的信,站在门口说我是谁。于是大家都站起来,有人给我倒水,在水里放了茶叶,福州的绿茶。
那时我正患胃病,说是胃寒,不敢喝绿茶,一喝胃就痛,但我不敢说,只是把杯子抱在手上。
有人说,先住下来吧。我记不清是谁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不敢正视那些站起来欢迎我的编辑老师们。
于是有一个人把我领到对面的房间。也是一间教室般的大房间,绕墙摆着三张床,每张床前都有一张桌子。
所有东西都是阴暗的,我不知为什么感到有点冷。
好像是初秋,刮北风,天阴沉沉的。
我的心情很不好,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

带我进来的人好像看出我的心情,微笑地安慰我:“就这样,我开头来也这样,不是想象的样子。住下来就好了。这里人好。”
这时,从对面床的蚊帐里钻出一个人来。那是一个小个子,他朝我友好地点点头。
带我进来的人说:“他叫艾青峰,部队的,也是业余作者。我叫黄文山,也是业余作者,在这里帮助看稿子。”
艾青峰是江西人。他说,他希望能多发稿子,因为发了稿子可以记功,可以提干,他家在农村,不想复员后再回农村。
他说得很实在,可我当时觉得他有一点俗,那时文学在我心中还十分神圣。他已经在《福建文艺》上发过文章,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发过小说。
但他这次稿子似乎没有通过,过几天,便走了。他的走,在我的心中留下些许凄凉。

我在编辑部住了二十几天,这二十几天我和黄文山几乎朝夕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友谊一直延读至今。
他当时是建阳麻沙汽车大修厂的工人,借调在编辑部。我的工作单位是省汽车运输总公司漳州公司,都是省交通厅直属单位。
我去过麻沙厂,那里离武夷山不远。我们又都是“老三届”知青,我高三,他高二。文山当时好像在谈恋爱,爱人在福州读书。
可他很少出去,白天在编辑部看稿子,晚上陪我聊天,天南地北,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有几个晚上,那大多是星期六或星期天,他要出去会朋友,临走前,他向我歉然一笑,问我福州有没有朋友。
我对他说,你去吧,我也要出去走走。他这才放心地走了。
我到编辑部是改稿的。《福建文艺》好像不久前在龙岩开过改稿会,庄东贤就是在那里给我写的信。

这一次“改稿会”是专为我一个人开的,编辑部的人全都来关心我。只是不见庄东贤,好像出差去了。
我记不清是谁先和我谈稿子的,也记不清编辑部的老师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
张是廉是拿着稿子进来的,文山说他是小说组组长。张是廉的个子不高,走路双肩有点向上提,稿子在他的手上抖着。
我觉得他是横着走进来的,我有点紧张。但他笑起来很可爱,满脸皱纹,双肩也随着笑声抖落下来。
我记不清他对小说提了什么意见,因为我现在连我那小说什么题目、写什么都忘了。
我只记得他说到人物、情节、细节、语言。我第一次把这些词当一回事记在心里。
当时我对人物、情节、语言还能理解,细节是什么弄不太清,又不好意思问,只是不停地点头。他见我点头也点头,点了头便笑,笑出声来。
他的笑声使我感到很亲切,接下去谈话便离开稿子,显得很随意。
以后我每次到编辑部,总是喜欢和他聊几句。

老张喜欢谈过去在福州一所著名的中学时的生活,那段生活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好像就是在那里参加革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
我非常羡慕他的那段生活,它使我想起初中看过的一部叫《我们在地下战斗》长篇小说。
有一次,我的一篇小说在省里得了奖,领奖的时候碰到他,他背靠窗,双肘向后顶在窗台上,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你越写越好了。
我想说,这都是编辑部的培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看着他傻笑。他看我笑,笑得更开心,还说了句,青禾啊青禾。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
不久以后便听说他退休了。退休后还见过面,他说他学会打桥牌,还参加比赛,得了名次。说着便笑,还是满脸的皱纹。
季秉义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帅,戴着一幅很好看的眼镜,风度翩翩,很像大学教师。他坐在床边和我谈稿子,给我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什么叫细节。
他说了什么是细节之后说,什么都可以假,就是细节假不了。
他还说有时一篇小说,什么都忘了,就是一两个细节让人忘不了。
他还谈起契诃夫,问我有没有看过契诃夫的小说,并建议我读一读当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两篇小说,是叶文玲和萧育轩写的。
我记得我看了小说之后,又改了一遍,他看了很失望,说越改越糟,说得我很沮丧。
后来,记不得在一个什么场合下,他对我说,看来,小说是教不会的,只能靠自己去悟。
他说的大概就是当时的情形,大家都为我出点子,都希望我能改好,结果适得其反。

老季最后“枪毙”了我的小说。
“枪毙”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文山告诉我的。他说主编苗风浦是个老干部、老作家,他写过一篇小说叫《二十五响拔壳枪》,被翻译成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他很严肃,不苟言笑。稿子的生杀大权在他的手上,他说不行就不行,“叭”地一声,就“枪毙”了。
我没有跟老苗说过话,只是远远地看他走过来,走进主编室。他的个子很高,人很瘦很黑,背有点驼。
有一次在楼梯头偶然遇见,他冲我点点头,又笑一笑。我发现,他笑起来很温和,没有“叭”的一声那么可怕。
从福州回来,我心灰意冷。没想到重新燃起我的希望是还老季。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大标语,老季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地上铺着写好的大红标语,他跳着进来,说出差路过,顺便来看看我,并问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收到我的稿子?
我手里提着排笔,不知说什么好。他说,你是很希望的,不写可惜。我于是又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
老季的话不多,但说话的嘴形很好看。
后来他当了《福建文学》的主编,又当了省文联的领导,说话的嘴形依然那么好看。
有一次我给他写信,想请他帮忙一件事,信寄出去之后,有点后悔,想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去打扰他。
但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把要办的事说得很仔细。这使我非常感动。
以后又收到了他的长篇《沿江吉普赛人》。奉着这部沉甸甸的著作,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想,有朝一日也像老季那样,出一本象模象样的长篇。

在那间阴暗而空旷的房子里,魏世英是唯一不和我谈小说的老师。
他进来时快下班了,一边和文山打招呼,一边拉过一只椅子坐在我的对面。他见我站起来,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坐下。
他斜坐着,翘着腿,一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勾在上面。整个形象像一只斜飞的风筝。
文山说他是理论组长、评论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话支开。
他问我的经历,问我的生活,当他听说我已经有老婆孩子时,显得有些惊讶。我说我已经三十一了,他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又指着文山说,你比他还大一岁。
老魏当时没有和我谈小说是因为他没有看过我的稿子,无从谈起。
但他后来一直关注着我的小说创作,在他的评论中几次谈到我的小说。这些评论给我许多启发,也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下来,与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后来,他又给我一个写《杨骚评传》的机会,我从来没有写过评传,他在信中鼓励我说,“你的风格很适合写杨骚评传。”
我于是写一部23万字的评传,写完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从小说到评传,对于我是一种挑战,不管好坏,我都感到满足。
后来,在评传出版之际,他又写了一篇恳切的序言,序言的第一句话说,“青禾是一位挚爱乡土的小说家”。
我一直把这句话作为是对自己的鼓励,冲着这句话,我也要永远写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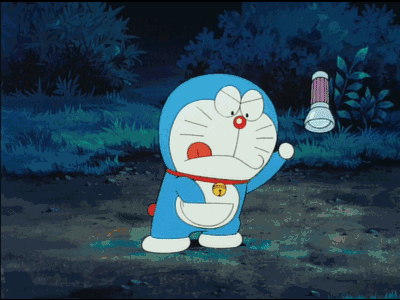
老魏的家在福州安泰路,原来是一座十分古老而典雅的大房子,我和杨少衡、海迪、赖妙宽一起去过一次,大家对那房子赞不绝口。
后来那房子拆了,盖了新楼,好像叫安泰花园。新房子也很漂亮,可我还是怀念那老房子,一进去就有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
我到他的新房子去过,在那里和他谈了我正在创作的反映解放初漳州小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初霁》,还谈了接下去几部长篇的构想。
他说很好,应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初霁》出版后,我就给他寄去。
不知道他收到了没有。听说他到新西兰去度假。我想他有一个很幸福的晚年生活。
蔡海滨在一个清晨,笑嘻嘻地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你从漳州来,你是漳州人吗?我说是。
他立即改用闽南话说,我是泉州人。我们便用闽南话聊起来。
他说他是厦大中文系毕业的,在漳州有几位同学,问我认不认得,念了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我居然认得。
他显得十分高兴,便问起那个人的近况,我把我所知道的全说了,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人聪明,不写东西有点可惜。
接下去便鼓励我,不管这次能不能改好,都要坚持写下去。他说,写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有意思。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时说话的神态。他的个子很小,很瘦,轻飘飘地落在床上,床板都没有动一下。
几年后,他为我写了一篇长篇评论,题目叫《他在寻找自己》,登在《福建文艺》1982年12月号上。

这一年,我在《福建文艺》发了三个短篇小说:《柔情似水》《无声的歌》和《凤凰街的早晨》。
文山告诉我,一年发一个作者三个短篇,在《福建文艺》还没有先例。这使我感到很不安。
我很认真地读了老蔡的评论,发现很多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文中看到了我自己,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他怎么这么了解我?
我第一次意识到,必须了解自己,就像打仗一样,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现在想来,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后来,老蔡当了主编,再后来,他退休了。他退休后我和漳州的几个文友去看他,他十分高兴,说了许多话。
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十年前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写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退休了,解脱了,也来读读书,写一点东西。
他的爱人在一边说,还写?他便笑了起来,不写不写,享清福享清福。我们都说,有这么好的房子住,真是享福的时候了。
没想到不久之后,便听说老蔡生病。还来不及去看他,又听说,去世了。

我们漳州的几个文友让《福建文学》为我们代办一个花圈,表示我们的哀悼。但我知道,花圈并不能表示什么,真正的怀念永远在心里。
郭风是在一个下午来到我的房间的,他站在桌子对面和我谈小说。
他的莆田腔很重,他说话时,我要站起来,他说,你坐你坐,我习惯站着,不要客气。
我于是又坐下来,仰头听他说话。他说得不多,但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写作就是要用“心”去写,“心”。
他还用双手比了比自己的心窝。他走后我问文山,他是谁?文山十分意外,你不认得他?他就是郭风啊,《叶笛集》的作者!
我于是更感到不安,一个这么著名的老作家来关心我,启发我,我还写不好。文山说,没关系,郭老很随和的。
三年后的冬天,郭老到漳州,我到宾馆去看他。
在路上,我有些犹豫,郭老还记得我吗?没想到一见面,他就叫出我的名字,并且说,你写得好,写得好。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那时我的短篇小说《春水微波》刚刚被《小说月报》转载,他说的大概就是这一篇小说。
我一直把前辈作家的关心作为一种动力,特别是郭老的那句用心写作的话,我将记一辈子。
写作不用“心”就不是地道的写作。
对于郭老,我一直感到歉然的是,在漳州宾馆的那次见面,我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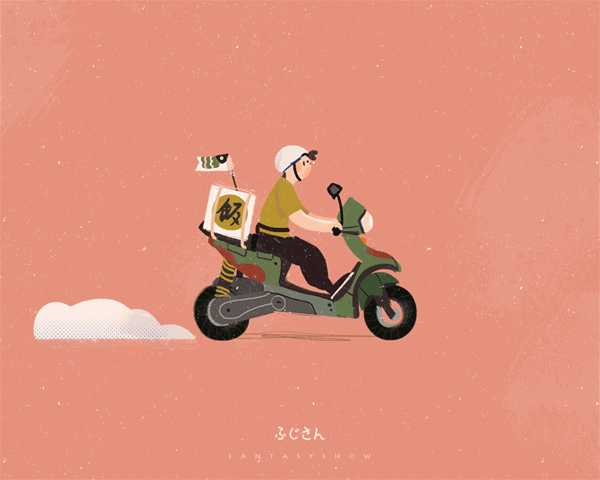
那天风大,我去拜访他时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有点怪,是过去电影里特务们常戴的那种三角形的鸭舌帽,话剧《青年一代》中的老工人也戴过。
那是我们单位一个人从西安给我带来的,很新鲜,便戴上了。他看到戴着帽子的我,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也许这只是我的错觉。
我想,以郭老的纯真和朴实是不喜欢造作的,而那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的确有些造作。我恨死了那顶帽子,从此不戴。
这次稿子最后没有改好,我的心情很不好。
临走时在一楼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门口,遇见庄东贤。他一边打着身上的灰尘一边问我,没改好?我说,没改好。
他笑了笑,带我走进房间。那是《福建文艺》的资料室,他正在那里做整理工作。
他指着满屋子的书刊对我说,“你看看,那一大堆都是过去的杂志,里面有多少文章,谁还记得它们?一两篇文章发和不发,实在算不了什么。”
经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情好了许多。
他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在执着的追求中多了一份了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保持一种相对平静的心态。
一年后,在他的手上,我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到底谁合适》。
在我连续发了几篇小说,受到读者关注时,他大声对我说,你不能再这样写下去了,老是“他和她”,以后出集子,谁还看得下去?他就是这样子,从不饶人,但说的是真话。
这话使我清醒,我开始思考如何拓展我的小说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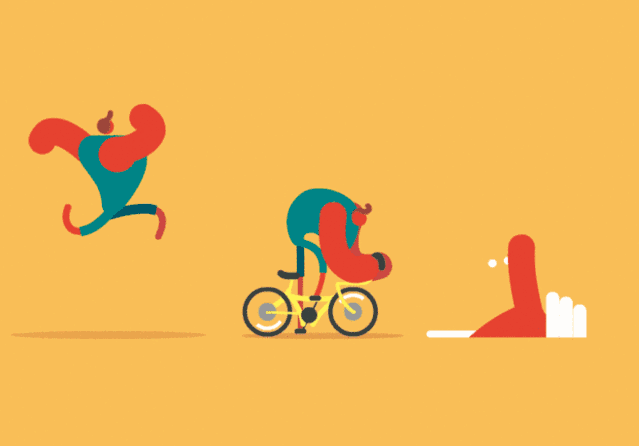
十几年后,记不得开什么会,我和杨少衡、海迪到他的房间去看他,他躲在被窝里,得意地对我们说,你们漳州“三剑客”全都是我发现的。
我们哼哼哈哈地笑着。的确,老庄是我们第一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没有这第一篇,就没有我们以后的作品。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整个改稿期间我的胃都不好,吃不惯福州菜,唯一喜欢的是粉肉,总不能天天吃粉肉啊。
天老不放晴,阴沉沉的,越来越冷。我要走了,文山把我送到楼下,送到路口。他什么话也没说,仿佛怕说错了什么,让我心里难受。
两年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下刷标语,办公室的人喊我,说有长途电话。
那时的长途电话是很金贵的。我跑上楼,躲进电话间。
电话是文山从福州打来的,他兴奋地对我说,你的小说上《小说月报》选目了。
我被他的兴奋所感染,放下电话,就到邮电局买一本当月的《小说月报》,《到底谁合适》果然上了选目。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说月报》来信,要选你的《春水微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