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诗歌:“伟大的声音常常从心底升起”

2020年是改变世界的一年,谈论2020年的诗歌确实显得有些沉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诗歌已经成为非常时期的伟大的发光体。从国内的诗歌生态来看,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并肩发展以及相互学习、融合已经展现成效,比如2020年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暨全国诗词诗歌学会座谈会、第二届中华诗词复兴研讨会、《中华辞赋》的改版等都显现出当代诗词写作、研究以及传播的新空间。
诗与真:
疫情时期的“诗人之教育”
“大多数作家则将许多时间消耗于种种折磨之中:想写,却不能写;想写得不同,却无法写的不同”,这句话出自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丽克在1989年的一次演讲《诗人之教育》。“诗人之教育”既来自诗歌内部,又来自社会外界的激荡。在艰难重重的非常时期,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最终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和活力?这让我想到当年奥登对叶芝及其时代困境的提问:“和我们自己相比,叶芝作为一名诗人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曾面临过怎样的困难?这困难和我们自己的相比起来有多少重叠之处?它们的相异之处又在哪里?”确实,我们应该在“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层面来看待2020年的诗歌现场。
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实则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在我看来,诗歌就是非常时期伟大的发光体。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很多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诗国际》网站自7月陆续推出《隔离时期,诗在飞行——中国诗人朗诵视频》(六辑)。当我读到澳大利亚诗人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写于疫情期间的诗《看见光环》和丽莎·戈顿的(Lisa Gordon)《同穿山甲一起封城》以及欧阳江河的长诗《庚子祭》、赵野120首的主题组诗《庚子杂诗》,我再一次感受到诗歌作为替代性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吉狄马加在4月完成了一首528行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不仅对人类灾难予以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剖析与反思,而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应了世界命题的诗学意义,“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地小心。/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

《隔离时期,诗在飞行——中国诗人朗诵视频》部分截图
在特殊时期,诗人从社会公民和良知道义的角度写诗甚至付诸社会行动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也是诗人不容推卸的责任之一,当然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评价诗歌自有其本体和内在标准,即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语言的民主”。质言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而疫情时期或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具有人类总体意识的整体性、方向性写作。
2020年,武汉的100多位诗人率先通过诗歌表达对疫情的人性剖析、生存思考和精神观照。伴随着恐慌与焦虑、爱心和援助,伴随着空前增强的民族凝聚力,几乎是第一时间,诸多文学机构、新闻媒体、文学刊物等纷纷推出“抗疫诗歌”专辑。4月4日春寒之夜,我读到了湖北诗人哨兵写于全国公祭日当天的诗作《清明公祭,闻警报志哀兼与残荷论杜甫》。当读到“我越老//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败叶/都是残骸,每一根枯梗//都是遗骨。而公祭警报/一声紧过一声,一片残荷//坐湖,就是一群杜甫/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一样的长安乱”,我的内心霎时被无形之手攫住,为之震撼并感受到了同样的阵痛与割裂。无疑,这就是一个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
在封闭、沉闷、压抑而又时时高扬的信念、信心和爱心的氛围中,“我手写我口”成为很多对生活具备敏感触角的诗人的主动选择,这是“诗言志”传统的接力。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一部分“抗疫诗歌”从不同的角度立体化呈现了疫情时期人们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整个国家和医疗队伍在抗疫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令人心惊不已的感人场景,“紧握时间的药方”“我们都是沉默的亲人”(查干牧仁《我们都是沉默的亲人》)。
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且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公众心理产生巨大波动,诗人开始正视生死存亡对人和诗歌的双重考验。在现实面前,诗人和诗歌往往是虚弱无力的,“——这不是诗,因为我没有勇气/冲下楼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张执浩《这不是诗》)。在严峻的异常时刻,我们是应该发声还是应该沉默?是付诸于行动还是付诸于笔端?这是任何写作者都必须正视的“诗与真”的问题。
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简单粗暴的急于表达表层化的“常识”,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无生命热力更谈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新闻写作”,这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而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诗人的责任既是语言、修辞层面的又是现实感和社会学层面的,真正的诗人会同时维护这两个责任,“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更有祈祷和祝福——/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任何情势下的写作都是“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同时进行、相互砥砺的过程,只有“现实”而没有“诗”或只有“诗”而没有“现实”,二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导致褊狭的认知和窄化的表达。尤其是当愈发复杂的疫情和同样复杂的自媒体舆论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那么多差异巨大的资讯、故事、眼光以及人生观、现实观和世界观。此时此刻,诗歌必须起到净化心灵和说真话的作用,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刚进家门/儿子便丢下玩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被我一声呵斥住/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洗手间清洗出来/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隔离汝身,溃烂吾心/爱,也是一种病毒”。(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
总体来看,“抗疫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需要纠正和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是冲突、违和的,恰恰在很多重要诗人那里,这二者是时时共振、彼此激活的。诗歌的起点是个体感受、生命体验和真实情感,诗歌往往是从身边的熟悉之物开始的,进而辐射到更广的精神视域,而这需要诗人的襟怀和眼界,这最终达成的正是诗人之“真”和诗歌之“真”,也即所谓的“诗性正义”。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除夕》就是如此精神趋向的文本,一个看起来与往年无异的仪式却因为加入了关键词“武汉”而跨越了个人经验,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词语的照彻下获得感人至深的人性关怀以及跨越时空限囿的精神势能,“敬锅庄之前/父亲照例在门口/用杜鹃枝叶/燃起一堆火/开始驱邪/烟雾随他口诵的词/在古老木屋缭绕/不同的是/今年,这个普米老人/还念到了武汉/这一小小的变化/让我一下愣在那儿/忍不住热泪盈眶”。
“当代杜甫”:
聚焦现实的传统、热度与反思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意义重大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取得防疫胜利的一年。在此语境下,关注社会焦点、处理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尤其是“抗疫诗歌”“扶贫诗歌”“新工业诗歌”“新时代诗歌”成为写作热潮。中国诗歌网先后推出近60个专辑的数百位诗人关于“抗疫”和“扶贫”的诗作以及相关的深度访谈,其中王单单结合了“抗疫”“扶贫”双重视域的主题组诗《花鹿坪手记》受到业界广泛认可并将正式结集出版,“更为厚重、集中、强烈,更能给人一种知性的启迪与情感的冲击。毫无疑问,这部诗集不只表明王单单诗歌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当下诗坛而言,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思敬《花鹿坪手记·序》)。

2020年4月6日,BBC播放了时长58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人类和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以及穿越时空而来的伟大诗歌的回声。杜甫几乎从未处于他那个时代诗歌的中心,但是他却成就了最伟大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由此他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正如冯至所说:“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杜甫凸显了诗歌的传记学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意义,而这又是通过“日常景象”和“现实书写”来完成的,杜甫式的“诗事”“诗史”“诗传”的“现实”传统正在当下发生着越来越深入的影响。杜甫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尤其在2020年,向杜甫致敬的诗歌和文论也越来越多,正如雷平阳所说:“杜甫的意义不在于他写出了诗歌里的悲苦,在于他一直寄身在生活与诗歌的现场,他的写作剜肉泣血,呈现了生命渐渐耗尽的过程。比之于我们那些苍白的伪道士、用假嗓子高歌的诗人,他是我最敬仰的诗人。”《扬子江诗刊》的“诗学圆桌”分两期推出了王家新、雷平阳、张执浩、沈浩波和霍俊明的3万多字的长篇对话《“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从文学中的晚年与晚期风格、同时代人与精神共时体、史传传统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世界文学和跨文化语境中的杜甫正典以及涵括万象的终极诗人等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杜甫的当代意义。师力斌的专著《杜甫与新诗》则从传统与当代对话的角度对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整体反思。实际上,杜甫的诗歌写作也拓展了当代人对诗歌、现实和时代的多元理解,“现实主义”写作永远是开放的。当代诗人“发现”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写作求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各种立场和文化的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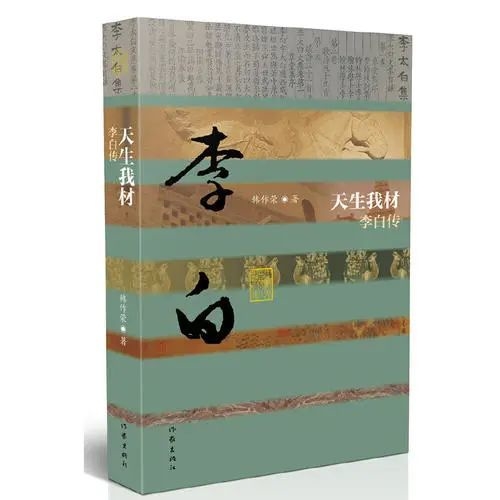
从传统与当代对话的维度,韩作荣的遗著《天生我材:李白传》以及美国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的出版更具代表性。韩作荣不只从“诗人”的角度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歌特质和精神世界,而且真切地予以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还原。哈金也强调“我们谈到李白时,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历史真实的李白、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制造的李白。”韩作荣从宽泛意义上将李白理解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持审慎和疑问的态度,在最大化的空间通过诗、人、事、史这四者立体化的对话实践还原了一个尽可能真实而复杂的李白。李白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而从“理想读者”的角度来看,韩作荣的这本《天生我材:李白传》也具有面向“未来读者”的质素和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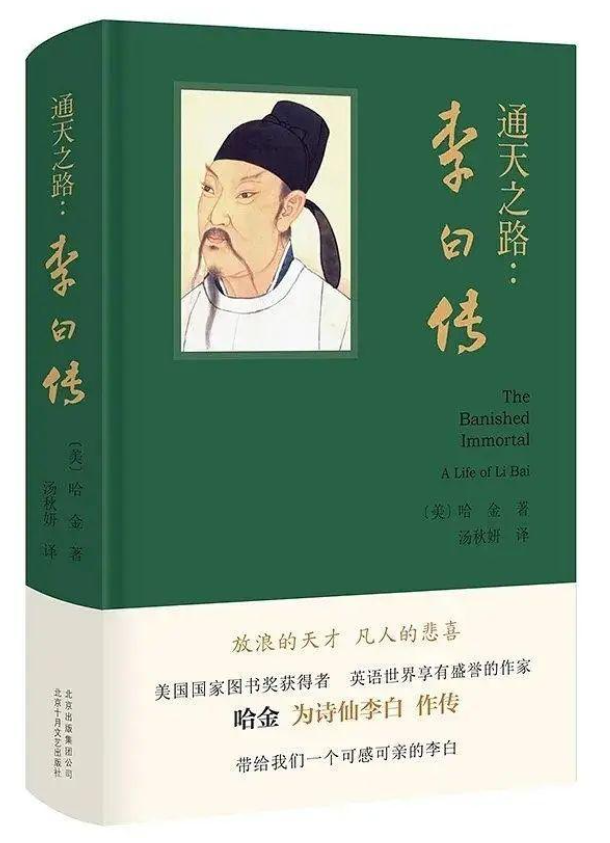
平心而论,抗疫、扶贫、新工业、新时代等聚焦社会热点的诗歌是很难写好的,甚至随着人们阅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诗歌的审美期待也越来越高。其中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同质化的表浅文本,它们既没有揭示出深层的现实,也没有发现现场中撼人心魄的细节和场景,而只是局限于新闻报道式的浮夸赞美。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或“现实主义的诗”。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王单单在谈到创作《花鹿坪手记》时所说的话可以作为一种参照:“我写花鹿坪扶贫系列诗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两年,我不是去体验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许多素材早已烂熟于胸,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主题在呼唤我的写作,而不是我要为了完成这个主题去写作,二者区别很大,关乎心灵的活跃与抒写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实感受力基础上的“灵魂的激荡”和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现实之诗、社会之诗。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评价一个时期的诗歌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化的认知装置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难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诗人尊重语言的民主,并以他们声音的音高或他们题材的普通性来显示他们随时会支持那些怀疑诗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实是,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谢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严峻时刻到来的时候诗人必须是见证者,当然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还不够,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世界诗歌”:
跨文化语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想象的参与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诗人较之以往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比如聂鲁达基金会诗歌杂志《笔记本》“中国当代诗歌”专刊出版,夏威夷大学出版的Mānoa国际文学杂志连续译介几十位汉语诗人作品,甚至诗歌还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种族触角和语种文化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译介的选择性、差异性、不对等以及意识形态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在跨文化、跨语际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世界诗歌”还涵括了“汉语性”“中国性”“民族主义”“东方主义”“第三世界写作”等问题。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而是“差异性对话”,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

世界文学和世界诗歌在2020年成为高频词,同时这也是伴随着“焦虑”的对话过程,“但是我们又特着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个概念叫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就像比较文学一样,世界文学也是一个学科,专门指的是被翻译的文学,所有不被翻译的文学都不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西川《“她让一个普通人,变成不可被替代的存在”》)尤其是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加之其诗集中文译本《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已经在2016年出版,所以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臧棣、麦芒、李元胜、倪湛舸、胡桑、金雯等诗人和翻译家以空前的热情谈论“世界诗歌”“翻译”的变化及可能性。通过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可以印证杜甫在长期的海外传播中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在“世界文学”视野和跨文化语境下,杜甫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越来越呈现了“正典”的意义。诗歌的现代性、本土传统资源、“世界诗歌”以及“未来读者”的讨论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此外,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等活动都聚焦于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传播和译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依然还是意味深长的。同样,一部文学译著的存在也证明,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真理与方法》)
为推动诗歌的向外传播,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同道出版社(Pathsharers Books)合作“汉诗英译”栏目,已累积翻译800多首诗作,中国诗歌网微信公众号和美国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网站每天同步发送。此外,中国诗歌网还与国际期刊Translating China合作“译典”栏目,在中国诗歌网和翻译先锋号同步推介中国古典诗词经典作品以及当代诗词优秀作品。“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一直是百年中国新诗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新诗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北岛、西川、王家新、黄灿然、傅浩、张曙光、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陈黎、李笠、李以亮、桑克、杨子、程一身、伊沙、马永波、晴朗李寒、远洋、欧阳昱、周瓒、王敖、胡续冬、范晔、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倪志娟、舒丹丹、袁永苹、薛舟、范静哗、张文武、宇舒、赵四、胡桑、包慧怡、连晗生、王东东、秦三澍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不小成绩。以“国际诗坛”(《诗刊》栏目)、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诗苑译林、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沉默的经典、果麦、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诗想者、小众书坊、“诗歌与人”、天星诗库、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浦睿文化、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拓展了诗歌译介的语种、区域。对于2020年来说,《新译外国诗人20家》、《世界抒情诗选:灰烬的光芒》、诗苑译林(7种)、《克罗地亚现当代诗歌选集》、《一百万亿首诗》、《玛丽安·摩尔诗全集》、《诗人与诗歌》、《俄国现代派诗选》、《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迁徙:默温自选诗集》、《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洛尔迦诗集》、《艾米莉·勃朗特诗全集》、《灵光集:兰波诗歌集注》、《无形之手:扎加耶夫斯基诗集》、《欧美四家诗选:里尔克、魏尔仑、爱默生、狄金森》、《弗罗斯特作品集》、《失群之鸟:泰戈尔诗集》、《这才是布考斯基:布考斯基精选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众多未来:乔丽·格雷厄姆诗集》、《贾雷尔诗选》、《佩尼希胶卷:西尔泰什诗集》、《月照静夜——艾利安·尼·朱利安奈诗选》、诗歌翻译杂志《光年》(第三辑)等都值得关注,其中有些重要诗人系首次在中国译介,这也印证了世界文学进入了一个“多点中心”的时代(沈苇)。
新的增长点:
技术传媒、诗教及少数民族写作
技术和媒介对诗歌的参与是有目共睹的,诗歌这架永动机是开放的也是更新迭代的。尽管鲍德里亚指认机器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小玩意领域”,不管你是否接受诗歌与媒体的互动以及生态新变,但是拟像、代码语言、物化社会以及奇点时代已经到来。显然,具有惊奇效果的科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逻辑正在改变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固有关系,甚至技术已然成为新世界的主导精神和宏大叙事。中国诗歌网与腾讯会议主办的“云时代:诗人与媒介生态”的直播活动在线观看人数超过23万,可见线上传播的影响力。
“潜在文学工场”(Oulipo)创始人之一的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在1961年有一个轰动性的“百万亿首诗”的实验,即10首十四行诗通过组合数学而生产出所有可能的文本总和,而百万亿首诗需要读者在每天24小时不间断阅读的情况下耗费长达两亿年的时间。《一百万亿首诗》的中译文直至2020年1月才正式出版。算法写作成为热点,当写诗机器人“小冰”“小封”出现并先后推出各自诗集以及“谷臻小简”已经初步具备了“评论家”的能力,很多诗人和评论家为此感到了不安、惶惑甚至愤懑。伴随着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变化而产生的“机器人读诗”“机器人写诗”以及“机器人评诗”,我们看到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自动化技术的“生产线”和拟态技术以及强化中的工具理性。显然,传统的或精英化的“纯文学”“纯诗”层面的评判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些“类文本”的复杂程度,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生产逻辑和符号逻辑。既然机器也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那么机器和人的写作最终面对的就不单是机器属性,而是人类的精神属性和存在的终极命题。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技术的广泛参与,诗歌越来越突出了即时性、视觉化和影音化的特征。诗歌的传播途径以及传播的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使得媒介化和电子化的诗歌传播与出版成为必然。

从更宽泛的“诗教”层面来看,现代诗的阅读和评价一直是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因而关于现代诗歌如何阅读、解读和评价也被推上日程,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之一”斯蒂芬妮·伯特的《别去读诗》(袁永苹译)从感觉、角色、形式、难度、智慧和共同体等六个层面深入讨论如何有效阅读现代诗歌,也打破了人们对诗歌的惯见。美国普利策诗歌奖与国家图书奖得主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手册:诗歌阅读与创作指南》(倪志娟译)则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声音、意象、诗行、节奏、技巧、形式、自由体诗、措辞、语调、语态等角度出发揭示了诗歌创作的秘密。雷格的《诗歌的秘密花园:20世纪伟大诗人名作细读》则从诗歌的抒情、现代性、形式、语言、意象、经验、讽喻、元诗等入手细读了经典名篇。在媒体、技术以及各种阅读需求的激励下,诗歌的出版和传播的渠道以及方式不断拓展。
2020年是“青春诗会”创办40年,所以在福建霞浦召开的第36届青春诗会具有格外的意义。而《诗探索》创刊40周年纪念丛书的出版则全面展示了这一诗歌理论刊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诗歌建设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好诗”第六季、“云南‘60后’诗人丛书”、“诗人散文”第二辑、“中国桂冠诗丛”、“诗想者”系列、“诗词名家讲”系列丛书、“橡皮诗丛”、“芒鞋”丛书、“白鲸文丛”、“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东北亚》诗丛、“我们”的诗丛书、新世纪诗典,《那些写诗的80后》《中国90后、00后诗选》以及《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集》《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第三说·二十周年专号》《微观中国民间诗刊2020》《湍流2019-2020年合卷》《四川民间诗刊档案1979—2019》《高车:昌耀诗歌图典》《于坚说Ⅰ 为什么是诗,而不是没有》《五万言》《修灯》《鲜花寺》《白鹭在冰面上站着》《茶神在山上》《长啸与短歌》《百年新诗1917—2017》《俄罗斯现代诗歌二十四讲》《我生来从未见过静物》《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新诗十二名家》《诗从细读开始》《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等作品,从诗歌创作、批评研究、史料、诗歌史叙事、访谈、随笔以及“诗人散文”等方面综合展示了当下诗歌场域。
少数民族诗歌在2020年尤为引人注目。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授予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西北辞》(马占祥)、《春夜,谁在呼唤》(满全)、《桑多镇》(扎西才让)、《逆风歌》(张远伦),“70后”和“80后”已经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打破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少数民族诗歌的印象,呈现出更为开阔和独特的生命意识、存在景观以及新时代视域下新的生活状态和地方文化景深。但有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有时过于局限于“自然景观”“地方生态”“民族文化”的外抽象化表述,丧失了基本的生命体验和想象力,而优秀的诗人总会在客观对应物那里找到与心象、命运以及生命意志力的对应。
近年来,在读诗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看重的是一个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智性能力,也坚信“诗”和“人”是不可二分的。显然,任何时代需要的都是“诗人中的诗人”的诞生。这类诗人往往是自我拔河、自我角力、自我较劲。这首先需要诗人去除外界对诗人评价的幻觉以及诗人对自我认知的膨胀意识,这类诗人尽管已经在写作上形成了明显的个人风格甚至带有显豁的时代特征,并且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他们对此却并不满足。他们并不满意于写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而是要写出具有“重要性”的终极文本,这也是对其写作惯性和语言经验的不满。吉狄马加的《迟到的挽歌——献给我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是一首关于“父亲”的挽歌,是永恒和重生的原型象征的浩叹,也是一个家族英雄的史诗。这首诗再一次回到了诗歌写作的起点和源头,即彝族人的生死观念、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以及整体性层面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终极对话和思想盘诘。这首长诗无论是在诗歌结构、语言成色,还是在家族叙事、历史想象力、经验以及超验的深度上都具有不言自明的精神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