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劼读《唐文治年谱长编》︱一位“开倒车”的大学校长
 2021-01-13
2021-0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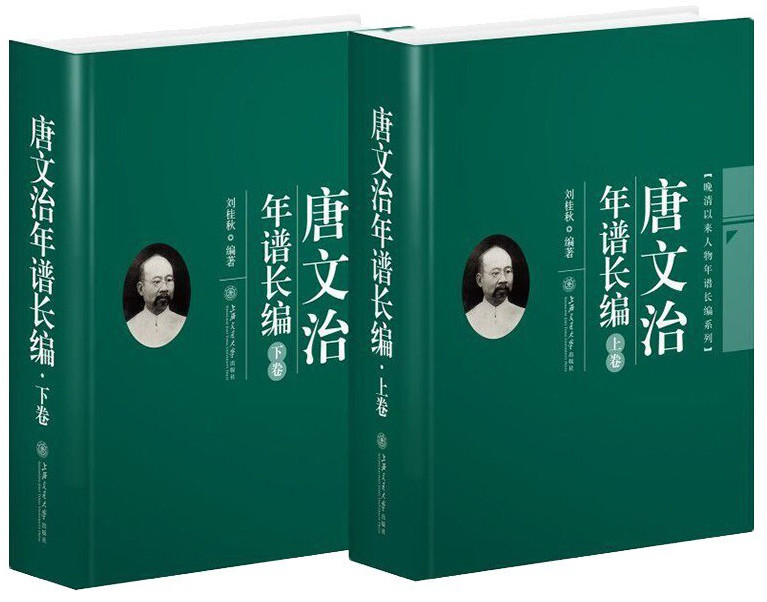
《唐文治年谱长编》(上下卷),刘桂秋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1251页,498元。
唐文治(1865-1954),著名国学大家,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官至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入民国后曾任大学校长。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引来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最扎实的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刘桂秋编撰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引用仅标注页码)。
笔者以前喜读传记,后感读传记不如读年谱,因传记写作可避重就轻、溢美隐恶,而年谱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没有了水分,从而更少主观色彩。一般以为编年谱易,其实,“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陈思和,《学术年谱总序》,《东吴学术》2014年第五期)。
一
年谱长达一百四十三万字,如此厚重,有几大因素。一是谱主高寿;二是唐宝刀不老,耄耋之年还忙于学校管理、参政议政、著述、慈善等事务,普通人退休后就无事可记;三是作者对谱主材料“穷追不舍”,广辑史料,尽最大努力去抵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年谱作者耗时十年,上天下地找资源,从档案馆、图书馆、数据库中发现诸多谱主未刊的佚文、函电、新闻报道及档案。当年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对唐文治的活动多有报道,作者借助《申报》数据库检索到三十多万字的相关内容,虽能提取文本,但准确度常打折扣,为此作者花费大量精力,比对提取版文本与影印版,以匡正错漏。民国年间,《锡报》《新无锡》也刊有唐文治的作品与活动,可这些报纸没有经过数字化处理,作者在无锡图书馆逐页翻阅老报纸,寻找可用内容,然后逐字录入。“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年谱的写作帮助甚大,作者从中找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寻找这些文献的过程是艰苦的,不仅考验作者的耐心与定力,也考验着信息搜寻能力。读罢年谱,深为作者发现资料、挖掘资料、考证资料的实力而惊叹。
正是基于翔实的史料,谱主的形象丰富而立体。如唐文治在南京乡试中闯关成功。唐自订年谱对三场考试题目都有记载,作者从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找到唐的考卷与阅卷者的批语收入年谱,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十八岁的唐文治的应试水平,也让读者对中国科举考试有更直接的感知。
编撰年谱时,作者注重资料的全面性与平衡性。如1882年5月6日,十八岁的唐文治在家乡参加了一次“群体事件”,七十来名太仓文人来到政府大院,面呈州县领导,要求阻止基督教牧师吴虹玉来太仓购屋传教。唐文治曾记其经过。年谱除采用唐氏所记外,又搜寻到当事另一方《吴虹玉牧师自传》的相关内容(42-43页)。用两造不同的记录,让读者对事件有更全面的认知。毕竟吴虹玉声名不彰,编撰此条目时,惯常做法是引用唐文治所记,而作者编撰年谱时,会以这个人、这件事为中心,生发开来,竭尽所能地去找与之相关的资料,由是他在《近代中国》1997年第七辑找到《吴虹玉牧师自传》一文,将不同立场的两方资料都载入年谱,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客观与中立。
作者的发散性思维与强大的资料搜索能力,使年谱有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如1894年,唐文治正当而立,其妻郁夫人因难产早逝,借助唐好友王清穆的《知耻斋日记》,作者呈现了唐文治的崇儒抑佛与当年的厚葬之礼:“然吾亲见所办棺木及漆工,费至八十余金,冠带衣衾之类,费至四十余金,虽事出仓皇,而未肯稍涉简率。发引之日,杠房亦费至四十金,凡可以从俗者未尝不勉力以求如礼,而止独延僧诵经一事,则决然不为。……同往夕照寺赁屋一间,为其夫人郁冰雪出殡之所,每月房金一两二钱。”(92页)一次丧葬,不仅花光了唐的积蓄,且让他债台高筑,多亏王清穆出城见了孙培元,帮唐借了“四十金”。
郁夫人去世时,正值中日大战,中方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东北,京城人心惶惶,纷纷逃离,唐文治虽在官场,但级别尚低,加之其母三寸金莲、行动不便,自身也刚丧偶,入不敷出,想要逃走,既无财力,又受母亲牵累,极为无助无奈。1894年11月1日《知耻斋日记》写道:“晨,访蔚芝,论及去留大节,我两人皆由科第窃禄于朝,际此国家有事,既不能尽一手一足之劳,稍冀图报于万一,乃以闲曹无职守为解,忍而去此,虽得性命苟延,尚何面目立于人世耶!故各以镇静不动相慰勉,死生有命,听之而已。蔚芝于《易》理有功夫,因请筮之,见其揲蓍挂扐不尽泥古法,筮毕,得大过之小过,蔚芝则谓非吉,余思驳象精微,难于窥测,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斯。”(97页)由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唐文治这位小京官在时代大潮降临时的焦虑不安,亦可得知占卜这项“基本功”在绅商界的流行。
二
“年谱”作为个人的编年史,一般被归入“谱牒学”与“历史学”范畴,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唐文治自小就喜读名人年谱:“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笙、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97页)七十岁时,他编撰印刊了仅五万余字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虽然简略,却为年谱长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
维新变法后,唐文治进入中央政府决策外层,对清末政治运作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王朝末年,风云激荡。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唐在总理衙门当差,身处旋涡的中心、决策的前沿,他对义和团的记载与评价,与现在的主流表述多不一致;唐在商部握有许可权时,切身感受到权力的巨大含金量与官场的腐败:“(1905)正月,粤商张弼士入都,请办三水佛山铁路,并在山东开办葡萄酿酒公司。余为具奏,邀准。张濒行馈余二千金,余辞之,至于再三,张滋不悦,则严却之。其后粤商张煜南请办潮汕铁路,闽商林尔嘉请办福州银行,均馈巨金,一律峻拒。”(296页)对欣赏自己的慈禧太后,唐敬中有怨:“是年(1905),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文治每感极而叹曰:‘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何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05页)这也从侧面证明,慈禧善于笼络高层却缺少政治远见。
1907年,当唐文治离开中枢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职后,年谱中所见证的不再是政府的运作,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缓慢成长:还在幼年的上海交大只有几十名教职员,许多院系领导由外国人担纲,学生所使用的专业教材都是英文版的,毕业生每年仅几十人。唐文治掌舵十三年,为交大成为世界名校夯实了基础。
作为中体西用的信奉者,唐文治强调学习西洋科技,不能排外,但他认为面对外来文明的强大冲击,更要尊孔读经,“一读十三经,二读国文”。可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四处一片“打倒孔家店”声,“废经者世奉为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唐文治认为这股反孔潮流危害甚大,造成了人心败坏,“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闵也。且夫我国之伦常纲纪,政教法度,具备于十三经”(唐文治,《中学国文新读本序》,《菇经堂文集二编》卷五)。然而,这套尊孔之论很不合时宜,唐文治只能在自己主政的校园里坚持读经尊孔,1917年8月27日的祀孔典礼尤为隆重:“祀孔乐章,……配以佾午,一时彬彬焉,雍雍焉,称极盛矣!”
一些受新文化洗礼的学生,认为唐文治校长所为是在“开倒车”。“以侯绍裘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生,对校内的尊孔读经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了学校里的孔子牌位。学生们的这一行动,使唐文治感到痛心疾首,终于决定把学生领袖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侯绍裘学业成绩优秀,作文尤为出色(曾在国文大赛得奖)。在唐文治的心目中,侯绍裘是一位有才华的优秀学生。可就是这位受过唐文治多年熏陶的学生,竟如此‘大逆不道’,他认为不开除不能维护封建礼教。”(《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70页)
1920年暑假,侯绍裘被开除,11月,唐文治毅然辞去主政了十三年的校长岗位,来到无锡创办国学专科学校。此时他五十五岁,且双目失明。
三
无锡国专定位于国学,相当于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方向,招生时不考数理化与外语,只考四书五经方面的知识。国专学制是三年,每年招生数在三十人到九十人之间,最多时,校内有两百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二十来人。三十年间,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不足千人,但它以“小而精”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人才:唐兰、王蘧常、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王绍曾、魏建猷、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许威汉、曹道衡、范敬宜、冯其庸这些文史大家都是唐的弟子,他们的名字让无锡国专与大牌学校相比也并不逊色。“大凡我国的文科大学或者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基本上都有无锡国专的毕业生,而且多是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培养国学人才这点上,国专可以和任何一所专科以上大学的文史哲系相媲美。”(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229页)
借助于这批学有所成的众门生,唐文治及无锡国专在消逝一个甲子后,仍为学界所关注。陈平原教授对无锡国专的办学成绩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传统书院现代转型的成功典范,并认为国专成功的背后有“无锡”元素,“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学术中国》2001年第一期)。无锡国专成就了唐文治,唐文治也成就了无锡国专,唐被认为是无锡人才引进史上最成功的范例。
刘桂秋先生2011年曾编撰出版《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此基础上,他对唐任无锡国专校长三十载的历史梳理得更为详备。可以说,年谱的出版,对当下的唐文治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较好的补充,为致力于唐文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详尽的唐文治的人生轨迹,展现了唐文治的国学教育的发展脉络。
四
作为当时的大儒,唐文治对儒学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他一生孜孜追求的便是正人心、救人命:正人心是办学、著文,让孔学深入人心;救人命则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有产者为灾民救急。年谱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为正人心,唐文治反复强调忠、孝等美德,可唐家却出了一个不孝子。1936年,唐的幼子、正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唐庆永离家出走,独自与情人去了成都,不曾给妻子儿子写过一信一字。1938年,唐文治得知庆永在四川成都后,作了“怀古”诗五首寄去,劝庆永回家,庆永不理,仍与情人过着同居生活。(吕成冬,《唐文治家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2页)与此同时,唐文治的三个儿子全都赴美留学。这也说明,虽然唐在无锡国专强调传统教育、推崇国学,可他也赞同物质层面上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这种中体西用的中庸思想为唐所坚持,却也在学界遭到杯葛。对此,唐的内在思想有没有张力?可惜年谱中未能呈现。这主要是因为唐的家书都遗失不存,年谱引用的资料多属印刷品,缺少未公开的日记与信函,使得唐文治的“本我”仍隐藏在冰山下。年谱中没有唐的收入记载,而唐本人1935年的自订年谱也从不披露其财产变动情况。按理说,唐在政府任职、在上海与无锡担任校长,都应有工资记录,可这一切都不存,也让年谱留下不小的遗憾。
上述信息的缺席,说明《唐文治年谱长编》尚有提升空间,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作者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就笔者所知,对学问之虔诚,对名利之淡漠,对朋友之关心,无出桂秋先生之右,正如虞万里先生在序中的评价,“沉潜笃学,刊落声华,不汲汲于课题之立项,每欣欣于史实之抉发,为学多方,深造独得,尤究心于乡邦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