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上海人沈昌文:最有趣的“破老头”,最温和的奋斗者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今晨逝世,享年90岁。解放日报记者曾在北京专访沈昌文。
世人若简单分为有趣、无趣,那自称“破老头”的沈昌文当属前者。这与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这与业界尊称其为“沈公”,并不冲突。关于他的有趣,业内盛传着颇多故事。记者与他面对面畅聊近3小时,触到更多的却是有趣背后的通透。
有人称之为外圆内方的生存智慧,而用他的话来说,这是特有的“上海人性格”。
记者发给沈昌文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写于2012年9月17日16时7分。
仅1小时后,回复邮件来了:确认接受采访,并请记者先定时间,“早一两天告我即可。我们可在三联书店门市大厅见面,然后我再安排晤谈的地方”。
很难想象,如此高效的网络操作,来自于一位当年已81岁的老人。
两天后,沈昌文又发来邮件,为了记者报道内容的“独家”友善提议:“你们是上海的报纸,可不可以多说说我在上海的情形?这是过去说得不多的。”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沈昌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善意——智慧是一定的,但更多的是,善意。
他接受过无数次采访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年轻的出版人,见他都要尊称“沈公”。然而,他依然善对每一次新的采访,甚至会设身处地为来访者着想。
9月20日,记者飞赴北京。在一见外观即知年头久远的三联韬奋书店,二层咖啡馆,邮件里自称“破老头”的沈昌文,背着双肩包出现了。
那里,就是他的主场。四处皆是熟人。他自若地打了一圈招呼,告诉记者,这些人分别都曾在三联任过何职。
刚坐下采访,他送了记者一本他写的书,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书背多了,帮我减轻点重量吧。”而后,看到记者怀里抱了几本刚在三联买的书,便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旧的黑布袋,帮着一并装起。
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记者发觉,尽可以畅快发问。他不会介怀,他无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他显然体察到了,便巧妙地说:“我也学过新闻的,当初一心一意想进《解放日报》。”
真的?记者问。
真的!他答道。旋即两人哈哈大笑。

沈昌文在书斋中 林环 摄
沈昌文小时候在旧上海当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教会他“趋避”,机灵地趋避;20年的上海生活烙印,还让他学会“开放”。他在沪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他的6年学徒生涯里,竟上了14所补习学校,而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时到深夜23时都能找到学习机会。清晨5时,他常去现在的复兴公园听人教英文、古文。他曾告诉记者,听讲《古文观止》时,他随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数十年难忘。
到了北京做编辑后,在上海所学,依然有用。比如,到三联书店上任后,他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于是出了房龙(美国通俗历史学家)的《宽容》,很轰动,又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蔡志忠漫画等;又如,他认为,不拘一格、放弃成见,才能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杂志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
采访一会儿后,记者随他去参观书房。虽离三联书店不远,他仍旧周到地为人着想,说:“你带着这么重的东西,我们打车吧。”
等出租车的时候,他又遇到熟人。他介绍,这位是读者,是在《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认识的——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一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让他习惯了一种“知所趋避”的独特化解方式,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
许多人总是倾向于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然而,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应同样值得敬佩。
如他所言,“我不是个勇士”;但同样如他所言,“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业内盛传着他颇多故事。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
2014年8月,沈昌文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海豚社出版。他兴致勃勃来到出版社,对着几位站起来向他致敬的年轻编辑说:“我预订一百本《也无风雨也无晴》,等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时,每人送一本!”当时把几位姑娘逗得只能傻笑,无以应对。
不知,成真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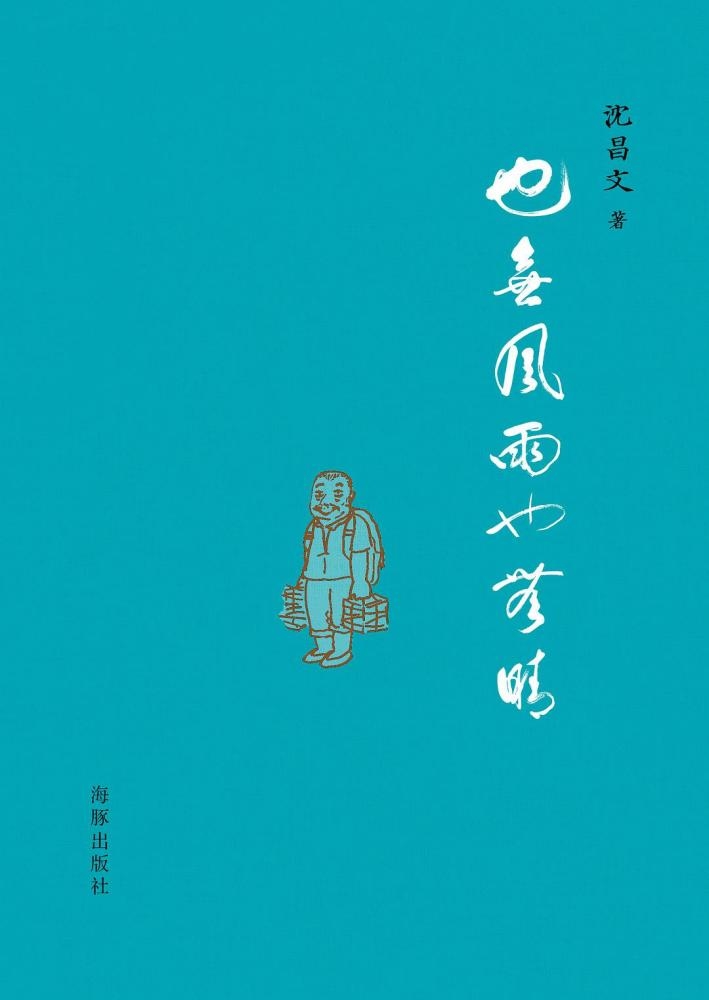
链接:《我一生做人,就是温和地奋斗》
刊于201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
沈昌文,男,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后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6年的工读生涯之后,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后参与发起创办《万象》杂志。
“知所趋避”
无论聊什么,他似乎总能聊到“上海”,并时不时蹦出几个上海话的词。他的普通话口音也有几分怪,带着北京味道的儿化音,也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这样的综合掺杂,像极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他显然惯于接受采访,因为“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但言谈中,他却惯用一种接近于“自轻”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屡称自己“懦弱”。这或许是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所致,让他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化解方式,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如他所言,“我不是个勇士”;但同样如他所言,“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记者:所谓“上海人性格”是怎样的?
沈昌文:人们爱说上海人“滑头”,并不假,但这“滑头”,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旧上海是典型的“黑帮”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我小时候做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更教会我趋避,要谨小慎微。当然,单单趋避也不行,还得机灵。
有多取巧,我举个例子。1960年代初,中宣部成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筹划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有名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后者是文艺思潮,我记得第一本是《在路上》。作为“内行的共产党员”,我被选上了。其实,我这时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日益增加。我掌握了一门技巧——从外形识别语言!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一两个月,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然后官员们都知道有个工人出身的会多门外语。其实是名声很大,没学多少。
再说说我谈恋爱时,有人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我于是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到了三联书店上任后,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它的专业分工。中国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而三联书店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冒出来,几乎“无路可走”了,只能是另找出路。毕竟是改革开放年头,思想比较活跃,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比如出了房龙(美国的通俗历史学家)的 《宽容》,很轰动;后来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被批准了。
还有蔡志忠漫画,那时我知道海外有出版漫画热,一口气买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等漫画很多种,比较下来,觉得蔡志忠的最好:通过漫画传播知识,比如《菜根谭》。从1989年到1993年,三联书店一口气出了近40种蔡作。蔡先生愿把版税存放在三联书店,我们正愁资金不足,这也来得正好,就买了一些职工宿舍。于是我的同事在总结我任内业绩时,常挖苦说主要是由于“卖菜(蔡)”。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一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说实话,对于读书明理,我从来不是学术向往。我跟人讨论问题的时候随时举某某书,仿佛我看过很多书。其实我这个“看”,跟专家学者说的读书是两回事,准确地说我是浏览。我的看书习惯是刚看这一本,看了3页,就看另外一本了。为什么呢?第3页讲到一个问题我感兴趣,我好多书呢,我一查,又查到另一本书……我经常自嘲是“做书商地看书”。
“大无”“大有”
在三联韬奋书店二层咖啡馆见面时,他送了记者一本书,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书背多了,帮我减轻点重量吧。”见记者已抱了几本书,便又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黑布袋,帮着一并装起。那个布袋,有些尘土,有些风霜的旧色。
人们往往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但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应同样值得敬佩,正比如他。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记者发觉,尽可以畅快发问。他不会介怀,他无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他显然体察到了,便巧妙地说:“我也学过新闻的,当初一心一意想进《解放日报》。”真的?记者问。真的!他答道。旋即两人哈哈大笑。
记者:20年的上海生涯还留下了哪些印记?
沈昌文:20年的生活烙印,毕生难以忘却。在上海,首先学到的是“开放”。我一辈子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多,但从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们,而且要同他们打交道。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首先为我启了蒙。我喜欢外国的“新鲜”,总想去学一学。在上海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你说,为什么我初中一年级就能做一辈子文化?是上海给我打了基础。
14岁,家里穷,没钱再读书了,我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磕头拜师,很辛苦,师傅会训人打人。但我很识相,并且是学徒中最有文化的,I can speak English(我能说英语)。虽说是半吊子的英语,但我敢开口,比如1到10我会用英语数,11就不会了,我却照样说1+10。当时是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兵到上海,来买首饰,我叫美国兵 Mr.Roosevelt(即罗斯福总统),他们听了都乐意买。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银楼大多关门。我却被老板留下了,端茶送水。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会英语,会写毛笔字,还会帮老板猜谜语。老板喜欢看上海《东南日报》的灯谜专栏,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案头,答不出的空白,我几次悄悄给他答出来填上去。记得一个灯谜是“山在虚无缥缈中”,打一古人名字。这个灯谜是“白头格”,意思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他想不出。我想出了,是孔丘,空的山嘛。老板很高兴。
那时老板闲着,常请人打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从苏北解放区来采购盘尼西林等药品、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的,叫我“小聪明”,有时让我帮他们收发信件,隔几个月还让我去生活书店买书买进步杂志。他们穿得很破烂,睡在我的床上,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服饰鲜明了,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饭。有一位苏北来的年轻人,每天打牌之余都努力读一本英文书。我便找来偷看一眼,原来是本桥牌手册。为了工作,不得不努力学习桥牌技巧,真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就渐渐成了他们的小崇拜者。
6年学徒生涯里,我以自学出名。那是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我受了祖母“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的教育,一直想离开学徒岗位,所以千方百计寻觅补习的途径。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点到夜晚11点都能找到学习机会。6年中,算起来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从速记、会计,到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和无线电。这还不算早上5点去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听讲英文、古文。听讲《古文观止》时,我跟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今难忘。
我到北京后还经常鼓吹上海一直以来的社会公益文化事业。我每次回上海,也都去复兴公园。我现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亚,也是复兴公园积攒的。
不过,我那时只是“可悲的银楼店里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我给师兄弟们读报,“徐铸成”三字中的“铸”,我一直读成“寿”,也从没人更正。将近半世纪后,我见徐老多次,却不敢把这则故事告诉他。
对了,我说学过新闻是真的。当学徒时,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声望,还可以晚上上课,我想去读新闻电讯系,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想不到这一来,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不再去“滴达滴达”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5点下班后,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到晚上9点才放学。尽管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学校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但我初中一年级程度,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譬如新闻写作,我努力半天,结业成绩只是50分。60分才及格,大出洋相。但俄文还学得不错,俄语老师想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但我无缘了。因为不仅筹不起学费,还要养活母亲。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娘姨(佣人)”,我再也忍不下心。于是,溜到北京了,从此离开学徒生涯。
到了北京做编辑,在上海学到的“开放”,依然有用。当年《读书》杂志面临思想大为解放的情境,我认为,时下可做的只有“三无”,即“无能、无为、无我”,只有这样才能不拘一格,放弃成见,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我们找各方面的人才,开设各种专栏,文学方面如冯亦代的“西书拾锦”专栏,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思想方面如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艺术方面不能不说丁聪老先生的漫画……编辑部内部,由此最得益的是赵丽雅(即扬之水,《读书》原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她后来自己总结当年是“师从众师”。
他微笑沉默,收起笑意,一字一顿:“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他关注海派文化。他的书房60来平方米,3间,领着记者参观时,他说一房间是文学,一房间是社会科学,还有一房间是“我喜欢的书”——此房间,3个书架,除了艺术类、养生类,另一即关于上海的图书汇总。不过,多为老上海的书。
他保留着老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偶在家掌勺,必定是浓油赤酱的上海菜,可惜家人都吃不惯,所以他时而去北京的美林阁吃“带甜味的菜”。他对记者挤挤眼睛说:“你懂的哦,美林阁,就是‘蛮灵咯’。”他还曾在办公室专烹上海红烧肉,用此类“大嚼”政策团结作者、同僚;如丁聪老人等上海名流,会闻味而来。
他最爱听的歌,正是他上海学徒生涯里唯一的娱乐,那时店里天天放。已然耳背的他,静极思动时就揣上“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出门搭公交,戴个大耳机,听着震耳的《何日君再来》;而被他称为“西总部”的书房,反正没人,邓丽君的声音更是放得几乎声震屋瓦。
他对此感慨为:“越老就越想回到从前,回到童年、少年,回到年轻时代。”
爬上6楼的书房时,他快步走在比他年幼近半世纪的记者前头,踩着运动鞋,迈得呼呼风声。尽管,喘声如风箱。
是的,他老了。然而,他藏了一颗已经苍老却仍倔强着年轻的心。
尤其是说起海派文化之时——他有一套海派文化系列书,一读再读,他说能满足怀旧欲。可是,能否建树一种“新海派文化”?他的建议是,上海文化+台湾文化。
他素来认为台湾出版业是大陆的“试验田”,因此台湾同行朋友极多。在任时,每逢台湾出版人来北京,他总要接待;其中一位出版人谈版权时,老引用上海人耳熟能详的“闲话一句”,他听了特别高兴。退休后,他每天观看两家电视媒体的两岸新闻;除了一年回上海四五趟,他唯一的外出地,大概就只有台湾了。
采访终了,记者请他用一句话概括评论自己。
滔滔不绝已两个半小时的他,微笑沉默了。几秒钟后,他收起笑意。
“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他严肃地一字一顿地说,“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