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学人访问记》:一位民国报人眼中的顶尖学者身影
 2020-12-17
2020-12-17

那是一个狂风呼号的下午,我冒着寒冷到他的住所去,与我工作家所形成对角的一个地方。他的住所是一个很宽阔宇,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许多小房,是很好的住处。我进门后,好像入了图书馆的书库,全屋充满了书橱,使我想起了他说“我是书堆里的人”的话。
85年前,也是一个冬天,一个25岁的年轻记者,敲开了一位学者的家门。此行的目的,是作为《世界日报》“学人访问记”的专栏记者,采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他对眼前这位历史学家的印象是:“他说话的态度总是很谦恭的,有时是关于学术方面问题,更是自谦地谈论着,而且有的问题,他也很愤慨,他的热血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关系而有所消退。”
这是“学人访问记”系列中的一篇。这一系列访问记,最早刊发于1935年的《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接续出版,前后连载了400余天。这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次深入访谈,也是对当时北京学人群体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其可贵之处,是透过一位民国报人之眼,借助其生动而不避琐细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代顶尖学人的鲜活身影。
这一系列访问记刊登之后,虽在当时颇受欢迎,但也终归湮没在浩瀚的旧报刊之中,静默于馆藏深处,鲜有人提及。直到85年之后的今天,经由一位名叫张雷的研究者整理录入,以《北平学人访问记》之名出版,才重新引起读书人的关注。

▍《北平学人访问记》位列2020年商务印书馆所评“十大好书”之首。
入宅采访 走近那片璀璨星空
在现代学术逐渐经典化的今天,民国学人被尊奉为“大师”的同时,也日渐隐身于各自留下的名著之后。他们天分极高,又得风气之先,仿佛天时地利人和具备,一切皆得之自然。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后来者的一种“成见”。我们习见了对他们的高山仰止,也耳熟于那一代人的学林传奇,然若想深入探究他们的学问所由,可能需要借助更多资料,对他们的履迹与所处的情境做更多了解。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平学人访问记》提供了许多丰富而珍贵的细节。
“访问记”的主体部分,是由一位名为贺逸文的记者完成的,他是《世界日报》的掌舵人成舍我的一员得力干将。“访问记”一共采访了69位学者,文理兼顾,既有如顾颉刚、沈从文、冯友兰、陈垣、钱玄同等人文学者,也有如曾昭抡、秉志、胡先骕等科学家,皆为一时之选。

▍“学人访问记”之《文字学专家钱玄同》
访谈由采访者登门拜访,与诸位先生详细面谈。一般先从学者的身世背景、求学经历谈起,然后再切入学者的研究兴趣与关注问题,最后谈及未来的工作和研究计划。由一篇访谈,呈现一位学者的林林总总与方方面面,又由这一系列访谈,勾画出一个欣欣向荣而各美其美的学术生态。
关于现代学人的人生叙述,无论是其本人的自述,还是后人的评传,其实已有不少,但这部访问记仍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它由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共同完成,因而天然带着采访者的视角,记录下了许多对于学人的观察、描述甚至是揣摩。
贺逸文是一位很自信的采访者,他从不隐身于采访之中,在访问记的起首,往往附有一长段类似采访手记的陈述,记录下他为找到学人府宅在街巷中的辗转寻觅,敲门而入后所见的院落景致,登堂入室时所见的家具陈设,乃至墙上的照片和书架上的书籍等等细节。他常常以第一视角铺展叙述,将所见所感仔细记录下来,令读者读来如同亲临其境。譬如他笔下的“苦雨斋”是这般情致:
西边屋里挂着充满了雨气的“苦雨斋”横幅,便是驰名文坛的苦雨斋。斋房共是三间,藏满了中文、日文及西文书籍。这里也有西式沙发桌椅,所以我想许是周氏的书房兼客厅,不过这里的清静幽闲,同几净窗明的境地,很可以使人留恋的。
这段带着“原景复现”意味的文字,仿佛引领今日的读者穿越而往,敲开尘封于时光的大门,去采访我们钦慕已久却未得谋面的大师。
贺逸文喜欢回味他对学人的第一印象,譬如,他对植物学家胡先骕的第一印象是:“他说话总是很刚强的”。胡先骕在说起自己出生那一年的情形时显得尤其沉痛,他说自己“是在甲午年中日战争时生的,那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国难发端的一年”,他“随着国家许多的沧桑到现在”。类似的描写,虽着墨并不算多,却在寥寥数语中,将学人性格中的复杂与鲜明,以点睛之笔道出。
他还很留意学者日常生活方面的细节。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学者的月薪颇高,生活上却多十分朴实,很少见他们的客厅里有什么华丽的陈设。历史学家王桐龄家中甚至没有安装电灯。贺逸文问他为何不安装电灯,他的回答是:“我和家人都是农村来的,早睡早起惯了,用不着灯。”后来才得知,他的特点正是在城市里过着农村生活。
得益于这些细节与细腻感受,访谈者将这些被我们后来者奉为大师的学人,还原到一处处具体的情景中,还原为一个个性情迥异、头角峥嵘的个体之人。我们不仅仅能在访谈的问答间领受到学者们的博识与睿智,也能感受到他们平日间的风姿、性格与生活,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时代。

▍《北平学人访问记》前插
人与情景的还原为何重要呢?我想,因为这是孕育经典的前提,是激发思想的触媒,是今日后人得以探究现代学术史的凭借。面对璀璨星空,除了仰望与赞叹,我们难免另怀好奇之心,希望能走近那片星海,去窥探那一束束光亮究竟何来。也正是在这种探询的视角之下,那些原先零星细碎却也更具个人化色彩的日记、书信、笔记、随笔,呈现了其他书写方式所未曾展现的独特价值。
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基础上,商务印书馆从2013年起,陆续出版了一套五辑共30种的“碎金文丛”,正是着意于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生长的语境。丛书所录为诸名家的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希望借由这些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探寻经典的“序曲”。丛书封面上金色LOGO中的“碎金”二字取自钱锺书先生的手稿。众所周知,笔记是钱先生问学的一个重要载体,以窥一斑而求全豹,“碎金”即借用此意。

▍“碎金文丛”第二辑
体味时代 大师们的隐微心曲
阅读这些大师们的各种文字,常能让人感慨于他们的学术生命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他们生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时代的易感者,甚至是先知者,却也常为大时代所裹挟。时代命题的急速转换,使得他们必须在各种文化碰撞之下,独立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这些在不同文化缝隙中的细微感受,往往深藏在他们的各种“侧面”之中。
今日学人皆知林纾是为人称道的古文殿军,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因为一出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而被群嘲为旧礼教的守卫者。然而人们又常常忘记其实他还是一位西方文学的翻译大师,大量文学经典经由他的译介才进入中文世界。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身份,也让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处于纠结缠绕之中。
在“碎金文丛”里收录了一本《林纾家书》,其中载有林纾写给孩子们的104封家书。他在信中自白道:“吾老矣,一切看破,惟教子之心甚热如火。”家书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载体,嵇康个性狂放,却在《家诫》里反复告诫10岁的儿子做人要小心,鲁迅慨叹道:“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可知有些境况下,家书或许是一把特殊的心门密钥。

▍《林纾家书》书影
林纾对孩子们的教导,可谓用心颇深,尤其是对于三子林璐和四子林琮的不同教育,体现出他本人身处于中西文化之间、身处于现实理想之间的纠结。在分别写给两个孩子的家书中,林纾对于三子林璐的教导,更偏于现实的生计,直言要他用七成功夫学习洋文,用三成功夫学习汉文即可,这样“将来始有啖饭之地”。而对林琮这个小儿子,他是寄予厚望的。在林纾临终前一日,生命已近垂危之时,他用食指在林琮手上写下:“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无疑,他试图将延续古文一脉的重任托付给这个小儿子。也正因此,在林纾写给林琮的家书中,叮嘱更殷切。他为林琮写了许多短笺,细细密密地吩咐着各种为人为文之道,还让他装裱成册,以便于时时观览。

▍林纾夫妇与林璐、林璿(摄于1904年)
正是在这些絮絮叨叨的家书中,林纾无所掩饰地向孩子们传授着处世之道,也时时透露出内心的忧思。他一方面秉持着传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却也必须面对西潮之下洋文、电影院等诸多新事物对于孩子们的冲击。他一方面怀抱着延续古文一脉的心愿,另一方面却也必须为孩子们未来谋生作出更现实的安排。家书中的“林琴南”,远比被新文化人塑造成的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要丰富和复杂。
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馈赠给学人以极为难得与丰富的生命体验,也赋予了他们以多维的学术视角。他们中的不少人,因身处浪潮之中,而具备了一种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新变的观察者,他们一面感性地体验,一面理性地思索。他们拥有的那些充满着新鲜气味的现场体验,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即时思考,都是后来者所尤为珍视的。
在“碎金文丛”中有一部非常特别的“讲义”。这本名为《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的小书,是林庚先生于1936年至1937年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的授课讲义。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对当时刚刚过去的新文学的“现场”总结,它简约而完整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自《新青年》发端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情况,讨论了文学启蒙运动、新文学独立、文学与革命等现代文学重要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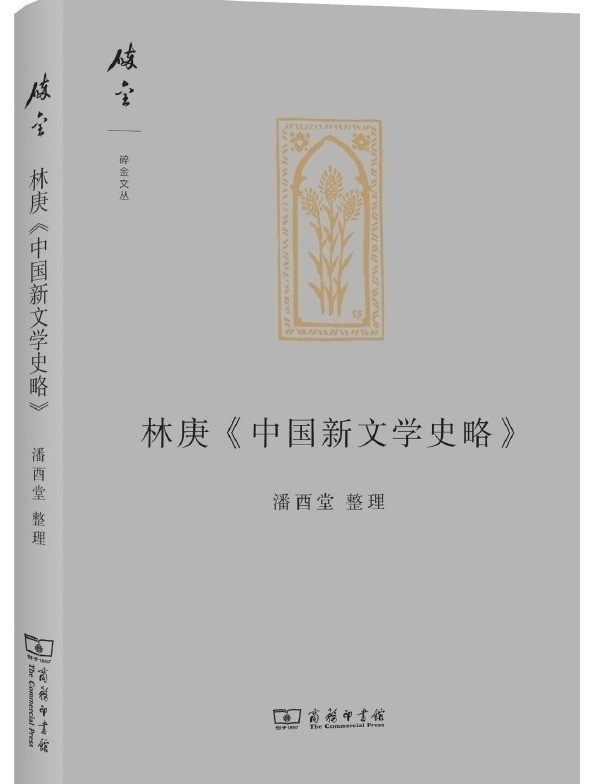
▍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
林庚先生本身在现代文学史上便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份,他一方面是著名的现代诗人,另一方面又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专家,他的“诗”与“学”可谓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他的创作和研究里都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天真气”与“洞察力”。他在讲义中的这段文字,最能体现那种情感与省察相交融的独特文学史风格:
这些虽然在今日已被我们忘记,在当时却是使新文学的风气弥漫于全国的每个细胞。在这样渐渐的滋长中,混沌的呼声变为具体的,幼稚的作品变为成熟的……那时一片文坛上的朝气,使得每个人都感觉到新鲜的气息,生命的活跃,如春天的河水,知其必将奔流于海了。
也正因此,他这份对其所亲历的文学大变革时代的记录,为后人提供了一系列原生态的文学图景,洋溢着弥足珍贵的新鲜气息和元气淋漓的现场感。

▍林庚先生在燕南园62号寓所前
这部讲义的出版也颇为曲折。这是林庚先生生前从未主动提及,也未出版的作品。讲义的发现,得缘于十多年前潘酉堂先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偶见《中国新文学史略》铅印线装本一册。从扉页林庚先生的墨笔题识可知,这本小册子是林庚先生赠送给罗根泽先生的。孙玉石先生通读这份珍贵的讲义后,大为赞叹,称其为一部极具价值的“新文学当代史”,并鼓励潘酉堂先生将其整理出来。于是,这本隐身于学人旧藏中的新文学见证实录,才终于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之中。
今日我们已很难揣摩林庚先生是如何看待这部讲义稿的了,也难以知道他在编辑自己的诗文集时又为何没有将其收入。或许是那些即时的感受未必成熟,或许是经历时代更迭之后很多看法发生了转变,皆有可能。在林先生其他传世名篇名著的比照下,这或许只是一部简略记录下他对文学变革的切身感受和思考的课堂讲义,可也正是这种在后世看来未必那么深思熟虑的讲述,透露出了一个青年诗人兼学者在双重身份中的复杂体验。
回应变革 学者们的济世情怀
面对时代激流的起伏与交锋,学者们不甘于仅仅成为一个亲历者、记录者,他们更愿将自己的学问与抱负,主动地投注于时代。这一代学人生长于国事危急之际,也多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因此常怀有强烈的家国心怀。他们中的不少人,热切地希望以一己之学改良社会、报效国家。他们是思考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行动者,这种对现实社会的热切关注,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学问思考另开生面。
在《北平学人访问记》中有一篇关于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访谈。访谈里,潘先生谈起他因运动不注意,而将膝骨跳坏,以致感染结核菌,最终被迫舍弃坏腿的经历。他的朋友们觉得这必定影响他的前途,可他自己却颇为达观。他甚至对着采访者开玩笑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被误以为是当时欧战受伤的战士而受到特别的优待,普通人对他很是恭敬,在芝加哥路上行走的时候,电车也常常为他中途停驶。身体的创痛经历,显然并没有影响他的问学心志,反倒更促使他自我奋发。

▍潘光旦(1937年在清华大学)
在“碎金文丛”中收录了潘光旦先生的一本文章集,名为《逆流而上的鱼》。书里辑录的文章大多是潘先生刊发于当时报纸刊物上的长短评,其中谈到了许多今日依然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如青年恋爱、幼儿教育、老人赡养等。可以说,这是一位身处时代变革之际的社会学家,以实际的一个个案例,针对具体社会问题,探讨着承续与新变的命题。
虽然这些文章发表于近百年前,讨论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时政,但很多文字今日读来依然富于洞察力和穿透力,这或许就是一流学者的思想魅力。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及当时国民政府强行废除阴历,不同于其他一些知识精英们高呼欢迎的支持态度,他却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怀有一种同情与理解。他呼吁那些所谓“移风易俗”的创设与革新,要在尊重习俗与传统的基础上推行:“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

▍《逆流而上的鱼》书影
报纸和杂志对于当时学人而言,多少也算是一种“新媒体”,是他们介入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潘光旦便热衷于通过撰写时评来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砥砺其观点。他曾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尤其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人来说,学问不可能凭空滋长,而须植根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同为中国社会学先驱的吴景超,也非常喜欢在报刊上发表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如在“碎金文丛”中收录的《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里,吴景超畅谈他对于农村与都市的看法。他一反前人将都市视为农村仇敌的言论,倡导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他认为在都市中兴办工业,可以解决农业人口太多的问题;发展都市交通,可以帮助农村货物的流通;拓展都市的金融机构以至于农村,使其成为农民资金的蓄水池,存取便利合时等。

▍社会学家吴景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潘光旦、吴景超,还是费孝通等诸多学人,都接受过欧美名师指点,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西方学科训练,并且在国外生活多年。潘光旦学成于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可谓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中国传人,费先生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然而也正是借助于西方学术体系的参照,他们发现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体味到其中复杂丰富的社会形态和自成一体的民间秩序,并不是套用西方理论便能解释的。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开启了认知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时代给了他们开拓眼界的机遇,而他们也以所学来回馈时代的厚赠。
百余年前的北京,可以说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文化之都。这里大学林立,名家云集,经典荟萃,古、今,中、西的时间与空间交叠于此,元气淋漓又风起云涌,孕育了中国现代学术最富学养也最具个性的一代学人。
王汎森曾在一篇文章中尝试回答“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问题。他提到了营造学术环境的重要性:学问的养成,并不只是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同样不可或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
确实,或许的确存在着天赋异禀的孤独天才,但真正的群星璀璨还是相互辉映的结果。正是在百年前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于北京,将外部的世事风云融汇为内在的精神体验,最终成为吸引我们不断回溯的中国现代人文原点。(责编:孙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