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我怎样自学诗词
 2020-12-03
2020-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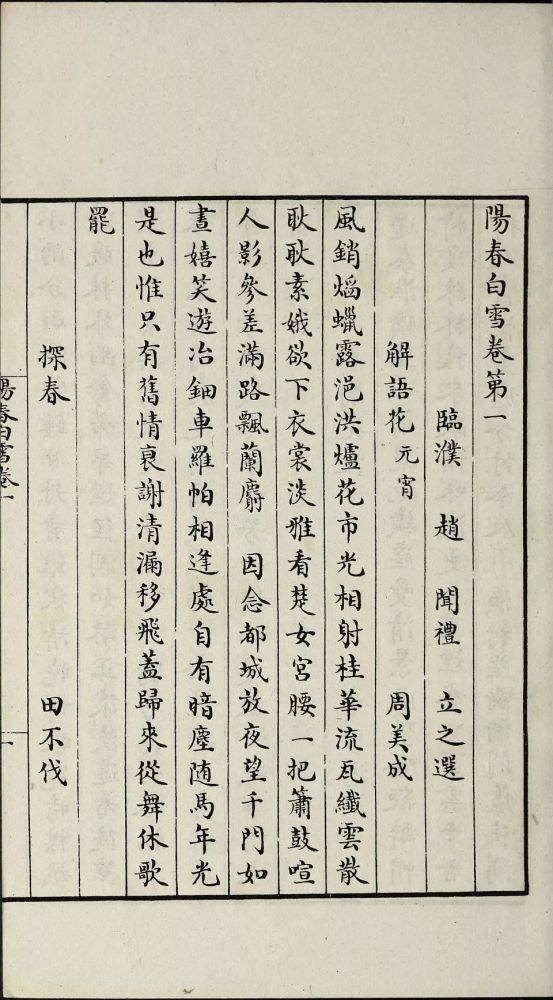
问:您是怎样自学的?研究与创作又是怎么结合的?
答:我没有很高的学历。十九岁温州师范毕业就工作了。教过小学、中学,后来教大学,专治词学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事了。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多少有点成绩的话,功夫就在一个“笨”字上。“笨”字从本,是我读书治学的本钱。记得温师的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其实为文、治学,面面都可作如是观。在温师就读的时候,我已经学作诗词,特别喜欢读前人的诗词。自己买不起书就向朋友借。当时比较难得的书如元遗山诗、黄仲则诗以及白香词谱等,我都亲笔抄录,供背诵之用。年轻时养成这种认真攻读的习惯,使我终生得益不浅。我体会到,如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心得,更谈不上治学和创作了。后来我在严州九中任教,四五年间,教课之暇,天天钻藏书楼,文史藏书差不多读遍了。有关唐宋词人行状的笔记小说以及方志资料,我都一一札入笔记本中,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研究资料的来源。广泛而有目的地阅读,是丰富学养的基本手段。除了阅读领悟之外,还要动手作札记。陶宗仪的《辍耕录》、顾炎武的《日知录》以及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都是这方面的巨著。作读书札记可以积累学问,加深理解。我从十五岁开始写日记、作札记,一直坚持,深受其益。如何作札记?我概括成“小、少、了”三字诀。本子不必大,便于携带;字数不在多,要言简意赅,理解要透彻。这样的知识才是扎了根的、会发酵的,能够产生质的飞跃。
求贤访友,转益多师,对于学问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温师毕业以后,听说南京高师办暑假学校,我就负笈千里,聆听了许多新学巨子的讲学,大开了眼界。词坛老宿如朱疆村先生以及吴梅、夏敬观诸翁,我一一登门拜访;同辈学人如龙榆生、唐圭璋、任中敏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密切联系。师友切磋,能启迪思路,鼓舞信心,对研究工作帮助极大。
诗词是一种文艺创作。我们攻治词学就是以它为评论和研究的对象。如果对其创作规律、艺术手法缺乏了解,便如隔靴搔痒,不易说到好处。比如苏东坡《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词歇拍云:“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况蕙风评云:“上三句未为甚艳。‘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遂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蕙风词话》卷二)蕙风此数语,指出了坡翁此词艺术手法方面的独擅之处,可谓具眼。非深知个中甘苦者,不易到此。所以历来的词评家,没有不是兼工创作的。以学人的识断来拓展词境,以词人的文心来丰富研究,二者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本是可以相得益彰,共促成功的。因此我在攻治词学时,并不废弃创作。1929年当我初识疆村翁时,曾以“青兕词坛一老兵,偶能侧媚亦移情。好风只在朱阑角,自有千门万户声”(论稼轩词)一诗持前请益,老人不以为谬,问:“何不多为之?”私衷深受鼓舞。迩来五十余年,每有所感,辄付吟笺。年来出版的拙著《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数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小结。虽不能佳,却也约略可以窥出自己攻治词学的一些经历和心得。知人论世,不知尚有一得之愚,可供采掇否?
来源:人民日报1982-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