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升的大地》:文学想象能否作为打开“中国乡土”的方法

正如吴晓东为《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所作序言中说到的那样,罗雅琳的这本新著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虽然作者谦称只是本“小书”,但这只是就篇幅设论,若就问题意识而言,这本书的抱负可以说是巨大的。从三十年代的斯诺、四十年代的光未然讲到八十年代的路遥再到新世纪的刘慈欣,作者所挑选的四个片断要么在此前的“乡土文学”研究里隶属“边缘”,要么则从未被纳入到“乡土文学”的讨论范畴中。两相对照,作者希望丰富甚至突破“乡土文学”既定的研究范式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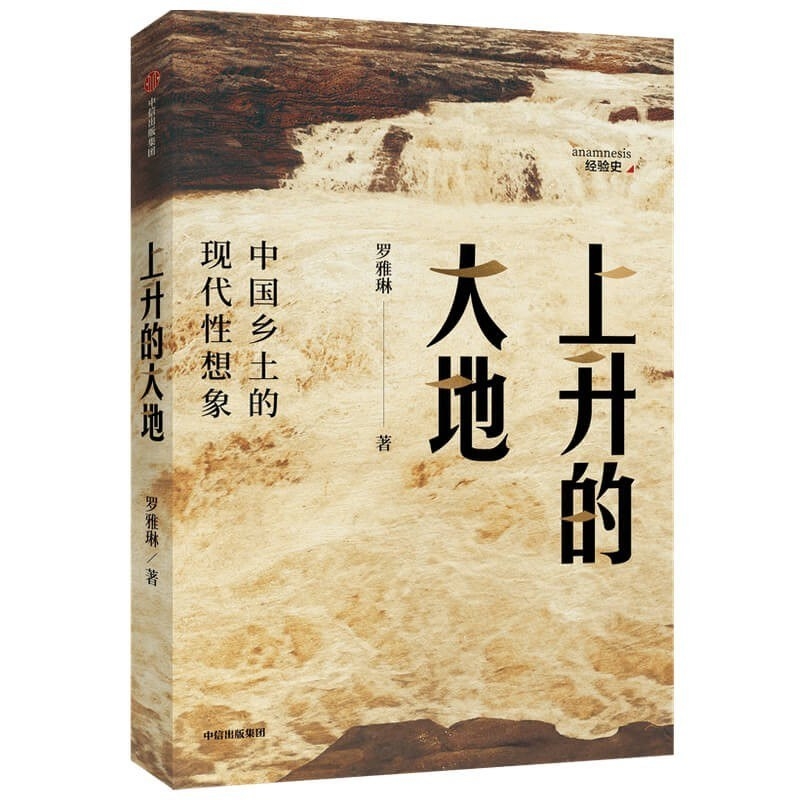
而细究来看,全书各章的研究对象并不能用“乡土文学”的既定概念来归纳。正像封底页三位老师为本书所作的点评——吴晓东和罗岗看重作者对“中国乡土经验”的捕捉,而罗岗同时又看到了“故园家国”的萦系,贺桂梅则认为这本书讨论的是“内陆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中国乡土”、“故园家国”、“内陆中国”,研究者三种不同路向的归纳并不构成冲突,相反其实都坐落在作者自己划定的畛域之内。温铁军认为:“中国问题在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这正是前述三概念之间最为内在的联结。从40年代根据地乡土实践到新世纪科幻里的中国经验,与其说作者是有意挑选边缘对象挑战既定范式,不如说正是在这一系列滑动的概念中,作者重新发现了“乡土文学”概念上的暧昧性和局限性,因而试图重新界定一个更大、更有效的问题域。
本书结语部分将作者希望对话的理论资源悉数托出,或许正可以看成作者重新界定的问题域的三次尝试。李欧梵所代表的(都市)“现代性”理论、费孝通所代表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以及刘小枫所代表的思想史研究,作者强调三位学者所提供的启发,但也不讳言自己的研究在不同层次上与前辈们的判断构成了对话性,虽然是部分的、仍在探索进程中的。而这份自陈本身也提供了读者进入这本书的三种视野。
我个人更看重这本书所展现出的文学与社会学互动的可能性。事实上从40年代根据地乡土实践到新世纪科幻里的中国经验,这刚好暗合了贺雪峰等人对费孝通学术取径的概括:从“乡土中国”到“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按:指费孝通)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乡土中国论域是能够展现中国的复杂性、形成文化自觉的研究对象,文化自觉则是决定前者能否被有效打开的思想前提,而二者都统一在知识界对自身的期待中。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这本书在方法上立足于“想象”,但在作者“是否还有人为大地上的农民思考一条上升道路”的追问里,文化自觉已经寄托在了“乡土中国”这个论域之中。
也正因此,这本书的书评可能不该由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来写,社会学的同代青年研究者的评价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作者携带着文学研究的方式突入农村社会学的传统论域,这正是罗雅琳一代青年研究者身上所体现出的综合性。与学科畛域相比,她们更关心问题本身,由左翼立场的现实关怀由此出之,力图以文学为起点把握现实由此出之,“青年人的自我反省”也由此出之。但也正因如此,检验这种“突围”有效性的尺度也应该放大。相比于文学研究范围内的有效性,我个人更关心罗雅琳擘开的这一精彩论域能否回应社会学者常常谈论的“重建农民生活世界意义”、“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深刻而具整体性的叙事”等问题,从而真正形成“文学想象”介入“乡土中国”议题的方式。毕竟她们已经走进了相似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轨道。因此,与其说我关心这本书里面的具体议题,不如说我更关心作者的方法论探索:文学想象到底能在乡土中国的议题里发挥怎样的作用?抱有现实关怀的左翼文学研究者,能否突破既定的学科畛域,与相似议题的研究者形成良好的知识互动,进而是社会互动?文学想象能够提供给读者一种打开“中国乡土”的方法么?
我认为这本书呈现出三种想象文学与社会学之间互动的方式。
作者既以线性时间顺序排列各章,以农村议题为核心线索串联起传统中国、革命中国与当代中国,那么发掘各自时段对农村与农民正面想象的诉求大概无需多言。以前二章为例。无论是三十年代斯诺(Edgar Snow)对西北边地可能性的积极把握还是光未然们对黄河符号的创造性改写,都是为了向读者证明我们曾经拥有一种“为乡村和大地赋予积极远景”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在这种叙述中,文学想象提供了历史资源,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可能也提供了“一种视野、心性与趣味的训练”。但如果单纯将文学表现问题视为一种想象力的匮乏,借助历史资源的开掘便可纠偏,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本书后三章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答。
在第三章中,作者借助细腻的文本分析,呈现出路遥笔下兼具物质与精神维度的农村与农民形象,一种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乡土”与“现代”兼容的构想。但我认为这一章更精彩的地方在于作者从路遥写作方式的“异数”中看到了一种文学传统的消失和文学版图重心的迭代,而这一文学表象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后“中国”内涵的变化——具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以沿海地区和城市为想象基础的,文学表征的变化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动力学的结构。所以,农村青年对《平凡的世界》的热捧,是从反面印证了他们曾经的知识渴求和现实中文化生活的匮乏。文学与社会学几乎是同时捕捉到了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证明着陈奂生们并不只有“上城”的“土气”,并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文学想象是以一种怎样模式化的方式捕捉着现实,并把现实制造成一种为读者消费的阅读效果。在这里,文学想象提供的是并不逊色于社会学的另一种触摸历史、把握现实的方式,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可以同时戳破话语表象(无论是文学话语还是舆论话语)而抵达问题的深层结构。
第四、五章则处理了更为贴近当下的文本。作者以归乡群体、离乡群体为大致分类,梳理出包括返乡笔记一类的“乡愁”写作、都市小资产阶层《春节自救指南》一类的“乡怨”写作以及打工诗歌一类的离乡写作在内的当代乡村书写。三种文本组成了现今文化舆论场域中对乡土的主要想象方式。从写作上看,作者大量引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反证几类写作方式的遮蔽。返乡笔记往往出于一个外乡人的视角,他们只能写出农村、农民现状与自己认知中的理想状态间的种种错位与不适,却“选择性忽视了农村在现代生活之‘变’中诞生的种种活力”,无力把握农村新出现的“新型伦理形态”。《春节自救指南》的“怨乡”写作体现着城市中国与城镇中国价值、趣味上的撕裂,都市小资产阶层“乡怨”一类的文化优越将价值观念的差异转变成为价值等级的高低,忽略了中国现代化转型所需要的时长。借助社会学研究所打开的时代孔隙,作者得以更新自己的历史经验、并重新进入一些公共议题,这里展现出了一种比较良性的文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关系。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一道,印证了现今良性文学想象的缺乏。

文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曾经是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经验。想象并非无凭之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北边地所形成的全新想象,得益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社会调查,得益于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苏俄政治与社会理论的引入,得益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想象力从来都依赖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想象型态。而在政治想象不足够清晰的时候,文学想象同步甚至先于政治想象的发展,成为某种“向革命开放的乌托邦形式”——希望小说发挥现实功能的激进知识分子们虽然身处革命的低潮,但却成功在小说世界里重新论证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合法性。
两相对照之下,今日文学作品中的农村书写则呈现出与社会学脱节的状态。贺雪峰在文章中经常申说的一个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而新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取消农业税,更带动了农村社会不可逆的变动。贺雪峰另一重要观点是,长时段来看,农村人口合理减少、农民进入城市是必然趋势,而在现实中,农民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也是基本事实。这种矛盾使得在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一定要保持稳定,农村才能成为“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这两种观点都以农村为本位,为我们把握农村问题提供了一种长时段视野。然而这种变动长期未能得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们的捕捉和认可,其实也就很难把握住对象内在的变化节奏而呈现出某种想象力的匮乏。这种匮乏更会呈现为某种思维方式的延伸。今日主流舆论场中,伴随着城市中产阶层、小资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僵化的农村认知已经逐渐转变为小镇和县城。“小镇做题家”、“县城中产”,逐渐成为新的他者。毕赣式的蓝调凯里,难以综合呈现当代中国(乡镇)的生机与危机。
杰姆逊认为文学是乌托邦。罗雅琳在印证当代中国良性文学想象的匮乏后,把目光投向了刘慈欣。在第四章的结尾和第五章中,她以一种近乎全身心的热情拥抱了刘慈欣文学,并将这种书写视为当代中国乡村书写的一种出路。在这里,“文学想象”成为寓言,书写出某种社会学研究难以企及的抽象远景。
我在这里无意质疑作者对刘慈欣作品的分析细节,但如果沿着文学与社会学互动这条线索继续思考,我们是否可以不急于将态度转向兴奋,而是缓慢消化这种来自“社会学的想象力”,对现实继续保有一个问号的空间。
以刘慈欣为出路其实并不能让我们避讳大刘作品中的“隐暗面”。比如,如果将《三体》中的叶文洁和地球三体组织仅仅视为“脱离民众的科学家”的理解未免有些简单化。叶文洁近乎极端性的行为起源于对“文革”的抗拒,而叶文洁向三体世界传输的代码,让人类在面临大毁灭的威胁的同时,也获得了走入宇宙的契机。正像《〈三体〉英文版后记》里写的那样:
科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够提出某种世界设定,让现实中邪恶和黑暗的东西变成正义和光明的,反之亦然,这本书(以及它的后两部)就是在试图做这种事情,但不管现实被想象力如何扭曲,它总是还在那里。
正义、邪恶与黑暗、光明,在刘慈欣这里是一个可倒转的装置。这或许是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人与宇宙之间浪漫的传奇”的原因。也正因此,以“先锋队”理论切入刘慈欣作品诚然有一定的说服力,现实的确给刘慈欣带来了全新的作品质地。但看破每个纪元后跟随宇宙毁灭、重生的程心才是《三体Ⅲ》唯一的主人公。这种太空诗剧般的写法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正是光明与隐暗面并存的结合体。“东方红”并不直接源于“煤油灯”。
反观第四章,作者分析乌鸟鸟《大雪压境狂想曲》诗作,认为展现出了一种关怀着他者、远方和“我的祖国”的视野,展现了“诗可以群”的政治可能性。但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
超负荷的运转/致使它们失控了。泄漏的雪花/成吨成吨地飘落。/我的祖国顷时惟余莽莽。
即使存在“诗可以群”的政治视野,打工诗歌中“群”的可能也是以一种相当压抑、扭曲的形态传递出来的。这里对毛泽东诗词的化用写就的最后一行确实是神来之笔,但在“超负荷”“运转”“失控”“泄露”“成吨成吨”这样的工厂修辞下,“反讽”可能是比“关怀”更为恰切的解读方式。毕竟,正如作者在这一章稍前部分所揭示出的打工诗歌常出现的人称断裂现象所揭示的,在这首诗里,诗人在雪花中看到的也还是“我”的祖国。发现上升的契机的确容易让人兴奋,但我们可能还需要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再停留一会儿,才能寻找到更为真实有机的力量而摆脱乐观背后质地的单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认同作者在第三章的精彩归纳。既然这是一个“交叉地带”,我们便要认清城市与乡村是现代中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但又已逐渐成为各方面不断相互渗透的动态空间。而这种综合与上升也注定是相当艰难的历程。我们应该在“交叉地带”再停留一会儿。
文学想象可以像社会学一样,提供一种触摸历史、把握现实的方式。文学想象的匮乏能够反证社会层面某种想象力的匮乏以及既定思维方式的僵硬。文学想象作为虚构,提供并放大了任何研究背后的政治诉求,呈现其“乌托邦”性,以上是我从这本书中收获到的三种可能。我认同前两者,而对于第三点,则更想表达一种文学想象与社会学所提供的想象力持续纠缠的愿望。
作为一部由四个断片拼合在一起的研究,我其实很期待作者补足漏掉的部分,或许在补充过程中,作者能够反思出文学想象介入乡土中国议题的新方法。比如,我很期待作者将跳跃过的延安文艺和50-70年代文学补足,如果借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读本丛书》编者的概括,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晚清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50-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底层文学等众多方兴未艾的子领域,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流派概念,而应该看成是一种“特定的知识构造”的指称。在这一“知识构造”中,反思现代性、打破文学的内外,关注文学史与社会史的互动,都是这些研究的应有之义。而关于“延安”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研究,正是助推其形成的引擎。作者在这种氛围里受到了文学专业的学科训练,前述研究的核心特点构成了她处理问题时的方法论前提,但如果感到不足够,且有进一步跨学科的渴望,或许更重要的是回到“引擎”段落,重新寻找新的突破和桥接可能。
如果作者在80、90年代莫言、阎连科等人以乡土为载体的作品身上“再停留一会儿”呢?以自由主义知识立场评价这批作品显然是作者希望克服与对话的对象,但如何形成一种更为恰当的历史评价?我们该如何理解《疲劳》的大地,《笨花》的大地……这些“大地”并未上升,但毕竟是他们第一次给予了“大地”以如此连贯、综合的图景。
而我更期待这个题目能进一步延伸到“非代言性质”的写作——所谓“快手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呼吁和渴望的农民在文化上的主体性,在短视频时代竟然变成了“现实”,——虽然其结果可能远低于知识界的预想。在未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他们成了所谓“下沉用户”。这是一次未经“提高”便由资本开启的“普及”行动,形成了一个算法主导下的分众性质的舆论空间。但借助直播和短视频,农民开始生产并输出属于自己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对热门视频的模式分析、叙事分析,对新的媒介和舆论空间的批判性认识,大概是我们尝试重新触摸并介入新一轮的“民族形式”,让“大地”具备某种“上升”可能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