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灵氛中的繁花、怀思与……诗的反抗


《午后的繁花》,陈建华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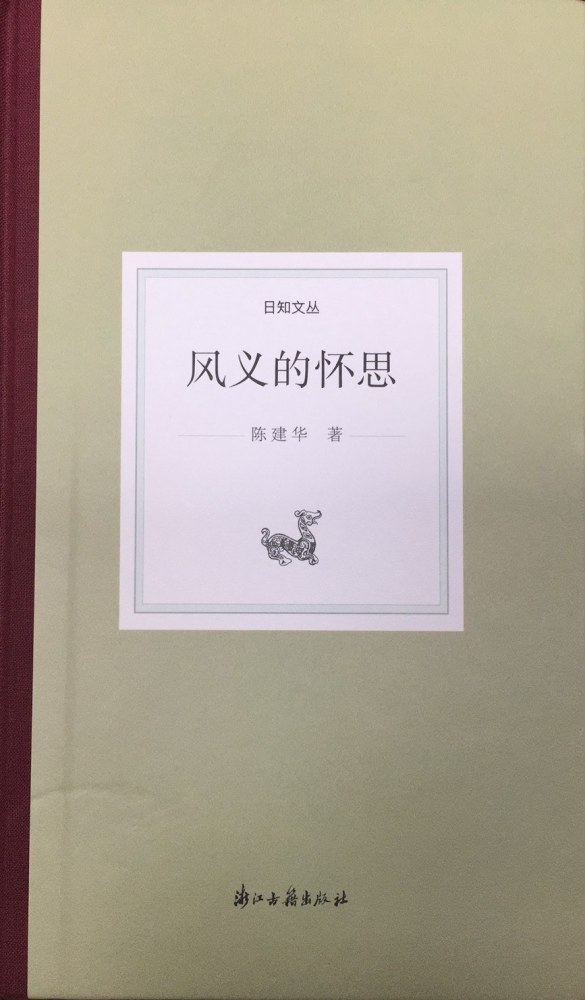
《风义的怀思》,陈建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版,160页,30.00元
陈建华教授的两本新著《午后的繁花》(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 月)和《风义的怀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同时推出,给我带来交织的阅读体验和惊喜。前一本是偏重谈文论艺的随笔集,后一本是追忆、悼念学术界师友的文集,两者之间当然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要掉点书袋,就是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所讲的,两个文本之间是镜子般的相互参照的关系,彼此之间形成一个谈文与论学的开放网络。作者说自己或许是应了“围城”的比喻,在学术与文艺之间滑进滑出。其实自其阐述文学的“革命与形式”的现代性之展开后,经由“从革命到共和”的文化转型,陈建华一直念兹在兹的是在诗(艺文)与史(融文学史、思想史、新闻报刊史、影视研究、视觉传播于一体的大文学史)之间的跨界探索,无论“繁花”还是“怀思”,指向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化风景线中潜藏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以及失落在大时代中的文心与学魂。
作者在《午后的繁花》“自序”中说这些随笔“多少带点文艺腔”,还说不断提到少年时代写诗的事,说明自己还是有一种文青的心结。在我看来这“腔”和“心结”早已不是捧在小文青手上的珍珠奶茶,而是在一个大学者与老顽童面前的那杯滋味悠长的下午茶——让我想起我们粤人喜欢在茶楼饮的那种“下午茶”,在细语嗡嗡、绘声绘色的家国旧事、江湖新传中尽情倾洒着慷慨与悲怆—— 在陈建华这里,则是从革命年代的少年颓废诗人到跨洋学术圈的记忆连接与芳华闪烁,如星火的烬余在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中又重新燃烧起来。从记忆中的文艺情窦初开到成熟的阅读经验,从大洋两岸的学问切磋到不忘初心的文艺感动,就这样如梦幻般地散落在这些散文随笔之中,在骨子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文艺与学术的“灵氛”。
之所以会有如此“灵氛”,与陈建华的“诗心”是怎样炼成的大有关系。十九世纪的波德莱尔在巴黎的街角锻炼诗的剑术,陈建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街角(福州路旧书店右边的一条弄堂)接受波德莱尔的诗的洗礼,在“文革”风暴眼即将卷至的时分追踪罗浮宫前的那只天鹅。从旧书店的“闲逛者”到郊区船厂中的一名被钉在黑名单上的小青工,陈建华的“诗心”是跨国文学影响和全能主义政治下的文化反抗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极为真实的个案。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像在寒冷的暗夜中背靠着背,围坐在仅有的火堆旁以等候黎明一样。这火堆便是文学与诗。怀着爱情,怀着希望,在绝望中又不甘心于绝望……”。(《风义的怀思》,77页)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旅日学者刘燕子在她主编的一本叫《蓝》的文学杂志中曾经介绍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活动,这的确是现代中国艺文史上不应忘却的一页。《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 写于朱育琳先生逝世廿五周年》和《与朱育琳先生私谈:波特莱尔翻译、翻译风格及其他》既是悼念之文,同时也是特殊年代中的文学史料,在我看来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还是回到“繁花”。一篇《悲剧共同体:舞台剧〈繁花〉观后记》,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骨子里的戏迷与评论家。“开头震惊之后便进入舞台世界,敏感中不免挑剔,生怕一树繁花被风吹雨打去……舞台上空荡荡的,没了闷锅里的情欲气氛,不免惋惜。然而银凤对小毛说‘做男人的,要勇敢’,为之叫赞。尽管这里那里觉得不足,三个钟头里把我神经吊足,情绪回应像全剧一样流畅紧张,尤其是场息之后剧情进展干脆利落,伴随李李的痛苦自述,高亢的音乐把我吊到山巅有点吃不消,最后沪生读信,是姝华的声音,落到‘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一句,顿觉五内震动,井蛙惊雷,舞台揭盖,通天透亮。落幕中掌声不歇,音乐升起。‘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在温馨回荡中渐次抚平心灵的风暴之旅。”(《午后的繁花》,第3-4页)好一个“顿觉五内震动,井蛙惊雷”,如此共情的投入使我好像也被吸引到这“心灵的风暴之旅”之中。接下来谈舞台的空间处理、道具与影像的拼贴变换、抽象与具象糅合的适度的先锋性、由沪语及苏北腔和台湾腔等语言交织出来的历史质地,以及关于在形式上重拾说书传统与在叙事结构、隐喻与节奏等方面的先锋性之间的把握,均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戏剧艺术研究修为;更敏锐与深刻的是对姝华的命运选择的悲悯和人性困境中的复杂性的分析和揭示,“唤醒我们的同情与思考”。
另一篇谈电影《图雅的婚事》也是一样,以“赖活”和“死缠”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影片所讲述的一波三折的爱情、生存与死亡故事背后的真谛,在爱欲与人性的层面上诠释了意志与情感的奇崛力量。从情爱的格套和欲望的宣泄中审视其意蕴、观念和美学特征的上升与提炼的可能性及空间,在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感情结构”中探讨文学和影视所表现的爱恨情仇与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机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是当年在哈佛修过电影课程的陈建华在文艺研究中的核心关怀和拿手好戏。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建华的文艺评论中亦时有关于政治与反抗性的论述,自是他从“革命”与“共和”一路走来的精神底色所在。前面谈到陈建华在少年时代接受波德莱尔的诗的洗礼,在后来的思想洗礼中他同样接受了波德莱尔作为诗人的革命气质。 在他看来波德莱尔虽然不信仰共产主义,却生来养成了反抗的性格,身躯里流淌着平民无产者的血液。他在“二月革命”中兴奋莫名,背着枪出入于硝烟弥漫的街垒之间,“作为一个诗人,他酷爱自由,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压迫,投入‘革命’是一种反叛的激情宣泄……。”(同上,107页)1957年值《恶之花》问世百年,中国的《译文》杂志组织了纪念专号,刊登了陈敬容翻译的九首诗,“其时反右运动方兴未艾,这一纪念活动似是个异数,也是《恶之花》中确有抗议资本主义的内容而与马克思主义搭界之故”。但是他指出与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相比,为波德莱尔所眷注的非洲黑女、俘虏、被流放的、被遗忘的,却含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他非常同意普鲁斯特和吕夫对波德莱尔的评价:一个最富同情与溫柔、最人性、最民主的诗人;对受苦受难者寄予深刻的同情,实即对于社会的反抗。(126页)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天鹅》是献给雨果的,不仅呼应其‘人道主义’,诗中‘流放’的主题也实有所指。1851年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被流放国外。该诗写于1859年,这一年拿破仑三世发布赦免令,但雨果拒绝回国。”(126页)如果转换语境频道,把这段文字拼贴上去,波德莱尔与雨果的穿越让人泪目。高擎着《永生的火炬》,诗人陈建华向前辈致敬:“这一神圣的行列犹如诗的辉煌谱系,颇有中国人说的‘道统’的意涵。这些无名的‘弟兄’绝非等闲之辈,作为天使班中一员,行进在美的大道上,从他们那里他获得力量,也接受挑战。在美的森林中互相注视,死者的目光何等亲切!”(130页)加入到“神圣的行列”之中,获得力量并接受挑战!这是陈建华的文学与学术人生的自觉选择。
在《蓝火:玛雅·黛伦的镜像舞台》中,他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女导演玛雅·黛伦(Maya Deren)的一段评述很自然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性敏感:“二战之后,国际政治为冷战的意识形态所主宰。在这样的背景里,玛雅的前卫艺术有反政治的倾向,既批评好莱坞的机制化而主张电影的自由,对于笼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的迫害异见人士的文化政策,当然也不会认同。然而某种意义上反政治也是泛政治,近年来她的无厘头叙事、女性及边缘立场一再被发掘,其实与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融为一体。不过在玛雅身上尤为特别的是,她不像一般东欧流亡者那么政治化,这也情有可原,她离开俄国时仅五岁,对于反犹太与纳粹还没有什么记忆。另一方面受美国教育,看上去也完全美国化了,但她绝不尊奉‘美国主义’,反而对于少数族裔如黑人和亚裔的文化情有独钟,且达到如此形神俱合的地步,遂给她的后期生活和艺术带来特有的‘离散’色彩,伴随着坎坷和挫折。这不仅由她特立独行的个性所致,或许还同心灵深处的文化漂流感有关。”(24-25 页)在今天事关全球疫情、美国大选、欧洲反恐等议题的复杂舆论场中,对麦卡锡主义的认识和对“灯塔主义”的反思无疑是其中热点,但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对立叙事和选边站队只能说明了一种焦虑与功利的心理机制,玛雅·黛伦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思考。前几天和一位青年学子和一位教授在餐桌上讨论过这两个议题,深感欣慰的是在基本问题上我们始终有一种共识,即不能把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政治性议题简化为一种虚幻的期望投射,对所有的权力压迫、政治迫害和不平等经济的真相的揭露必须是无条件的,不能以站队来划线取舍。
关于民国时期著名报人陈冷,陈建华曾经写过专论《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载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其中谈到陈氏的某些“时评”(如1922年9月3日的《告纯粹之国民》)超越了批评的界限,可看做一种“言说行为”(speech act),即发言者不仅对时局作客观的批评,而且强烈干预现实,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发声,借以对抗专制政治”( 同上,240页)。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分析了陈冷所面对的不自由困境:“他似乎太明白在中国‘自由’的脆弱,与‘不自由’之间细如发丝,又太容易被腐蚀,而权力是坚无不摧的腐蚀剂。他知道随着蒋氏时代的来临,再要谈新闻自由等于与虎谋皮,因而作了一个断然的选择:远离权势。”(同上,249页)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就如粤人喜欢说的“一字甘浅”—— 一部现代新闻史和对新闻从业人的评价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在收入《午后的繁花》的《陈冷——报界“酷儿”》中,陈建华自言继续挖些“边角料”来当话题,其中我很感兴趣的是关于陈冷的“大义”“复仇”“自由”和“酷”。作者在前面先讨论了伯夷、叔齐所践行的绝对正义伦理,继而引述《上海时人志》对陈冷的评价“凡大义所在,不为利诱,不为势屈”,然后评论说:“我想这‘大义’与伯夷、叔齐所坚守的绝对伦理颇有殊途同归之处,特别在1930年,陈冷不受蒋介石的笼络,毅然脱离《申报》。”(《午后的繁花》,61页)至于“复仇”,听起来有点奇特,陈建华指出陈冷把《礼记》中的“父之仇不共戴天”作为“孔子之教”来为“复仇”正名,并且认为国民两大“病根”在于“无复仇之风”和“无尚侠之风”;而陈冷发表的《女侦探》《炸裂弹》《杀人公司》《俄国皇帝》等虚无党小说扮演了种种英勇壮烈的活剧,这类小说等于和革命运动中的暗杀潮私通款曲、输送精神弹药。(同上,68页)这是过去容易被学界忽视的问题,而陈建华在讲述中似乎也有一种热血的涌动。至于“自由”,陈建华认为对于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职业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的陈冷及其同仁来说,“独立是人格,自由是天职”;“陈冷说:‘中国今日之自由,与世界各国之自由,有大不同者。世界所谓三大自由,中国人或不能享。集会有禁制也,报纸有查封也,不犯法之身体,有羁押也。’(《申报》,1918年10月11日)由是可见‘公民社会’在中国途程艰难。”然后,引述了陈冷的这段话并认为其寓意深刻:“世间原无绝对自由之事。惟同一不自由,毋宁屈于威力,而不可自行贩卖。屈于威力,外虽束缚,而心尚自如。若自行贩卖,则并一己之意思而亦丧失之矣。斯实可谓世间最不自由之人。” (72页)屈从于外力而失去自由是一回事,最可怕的是连内心的自由也“自行贩卖”,就等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关于陈冷的“酷”—— 当蒋介石声称要一统中国、新闻界趋之若鹜的时候,陈冷敢于说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掌控《申报》后请陈冷担任主笔,他不答应并把薪金支票原璧奉还——作者连说了两个“够‘酷’”。
最后谈到曹聚仁对陈布雷、张季鸾被蒋收买甘做捉刀人的评论,认为“言下之意陈冷不受蒋的笼络,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比陈、张之流高出一筹”;“联系他的不‘自行贩卖’的许诺,在乱世中独善其身,求得内心的自由,也未尝不是一个智者的抉择”。(73页)必须说,这也是智者的真正酷评。
从《时报》《申报》主笔自然会想到后来的《明报》主笔查良镛,陈建华说“金庸心目中的‘报人’偶像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风义的怀思》,153页),并认为张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与陈冷的路数一样,但是在四十年代的复杂时局中变得更不容易。有了这番铺垫,然后直言在查良镛身上“体现了通观八方、公心远识、调适舆情的报人智慧……撇下个人恩怨的‘小我’而融入新时期一切‘向前/钱看’的‘大我’……”(同上,154页);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笑谈间恩仇俱泯,武侠小说风行大陆一路畅通无阻,文学桂冠接踵而来,金庸的“江湖”随心折叠开合,他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折冲斡旋,幸运并快乐着。“能在入世与出世、现实与虚构之间把智商与情商都能玩到这么极致的,也只有金庸,没有之一。”(同上,157页)在被转换的频道语境之中,只能拿捏到位,而且说得都还精准,已经不易。只不过令人无端想起陈冷,更知道什么是“不共戴天”的“大义”、不得“自行贩卖”的“自由”和敢于连连说“不”的“酷”,知道它们早就已经随风飘逝——那些跟随陈冷血的幽灵从来只有忧伤和悲愤,没有快乐。
面对新世纪一路全球性的“与狼共舞”的文艺美学景观,陈建华一方面承认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由是改变,且激发了新的思维空间与创造力,是全球化经济奇迹及其文化秩序的一种迷幻醉心的美学呈现,但另一方面他同时敏感地指出必须警惕的深渊:“到底是狼还是人?其间的分界何在?一不小心会跨入地狱。……在道德判断上就是似是而非、善恶不分,在认识论上就是认假为真”;“无论被当作可爱的坏蛋或可敬的英雄,在背后操纵的是变化了的游戏规则,即征服的意志、强权的崇拜。被遮蔽的是人性,所忽视的是‘诚信’”;“这么说的话,要嫁灰太狼的白领女性们会尖叫起来:别政治化好不好?在这个‘极度需要快乐的时代’,乐一下有什么大不了?是的,与狼共舞是现下的真实,拥抱狼性像走在钢丝上,在嘉年华狂欢中即使来不及思想,也需要高度的警觉和技巧,否则的话小心脚下的钢丝!”(《午后的繁花》,137-138页)这是诗人的政治敏锐和道德良知使然。
《“五四的女儿”:爱情、传记与经典》谈现代文学中的萧红、秦德君、胡兰畦和丁玲,革命巨浪中的性爱、政治和书写的“政治承认”及权力结构,尤其关注的是女性与文学正典之间的关系。
《胡兰畦回忆录》提供了一个在“革命”的“宏伟叙事”下的“他者”的自我怨艾和感恩的形象,“那种拥抱‘正典’的感恩与喜悦,混合着恩仇俱泯的宽宏,其复杂之处难以言喻”。(同上,155-156页)而秦德君与胡兰畦的遭遇相似,但她敢于发出出自女性的、饱受创伤的不平之鸣,敢于说出对“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的贬损之音。至于晚年的丁玲,“时时与改革开放的潮流相左”(同上,157页)也就罢了,作者通过她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杜晚香》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丁玲:当人们希望看到“莎菲”作为现代个性解放的象征而复活,对民族的劫难与人性的深刻有所反思而给世人带来启示的时候,莎菲却已经变成了杜晚香,“她更要使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枯燥乏味的丁玲”。(同上,159页)那么,不说也罢了。
《风义的怀思》收入作者悼念刘季高、贾植芳、章培恒、张晖、纪弦、韩南、朱育琳、赵景深等学者、诗人的文章,还有一篇谈在求学路上与魏斐德、周策纵、王靖宇、沟口雄三的交往,最后是《金庸的折叠江湖》。书名取自陈寅恪的“风义平生师友间”,“借此对幸能亲炙的前辈学者表达崇仰与礼敬,也有意与同道们矢志薪火传承而共勉”。(“自序”)这让我想起了帕斯卡—安妮·布劳特、米歇尔·纳斯选编的德里达《追念集》(The Work of Mourning, Chicago, 2001),该书汇集了德里达在大约二十年间为声名卓著的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吉尔·德勒兹、艾曼纽·列维纳斯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人所写的悼念文章,编者自述其目的是使人们关注与“哀悼政治学”相关的问题与难点。(见编者为该书所写的导论性文章《清算死者:雅克·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陆汉臻译)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时人们只能以沉默对抗悼念的编码与仪式;有时候则必须要让政治学从悼念的重新编码中产生出来,以对抗对悼念的另一种压迫。陈建华在《历史背面的断忆——悼念贾植芳先生》中说到在哈佛读贾植芳的《狱里狱外》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房》的感受:“放下书,向天空寻思,从一个牢狱到另一个牢狱,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巧妙而无奈的譬喻,时空的界线模糊了,交融为一体。语言的牢笼里,行动的主体在悲泣,而故土的过去却远为真切实在,铁窗里壮士在击筑歌吟。”(《风义的怀思》,19页)可以说,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学者,陈建华在骨子里始终关注的是悲泣的主体和壮士的击筑歌吟。
最后回到“灵氛”。“本雅明的aura 一词有多种译法,有的译作‘灵光’,有的作‘光晕’等,我更喜欢‘灵氛’,对我另具一种通向远古的蛊惑,尽管自知做不了‘上下求索’的醒世者。”(《午后的繁花》,211页)陈建华的“三十年集”《雕笼与火鸟》的序言有两段文字可以作为他“上下求索”的证言:“十八岁的时候写诗,伤感、颓废而唯美……后来不常写诗,却在记忆里发酵,每过三五年会写点回忆,回到那个黑洞里面壁一番,唤醒了伤痛和死亡、少年成长中莫名的震颤。如果还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就像一只火鸟,醒来冲天飞去,带着自由的歌唱,脚上的桎梏如纸片散落。”(同上,223页)“三十年来以研究文学为专业,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进而追寻集体‘情感结构’、‘视觉无意识’。无非世态人情,偶有魂销肌栗、一灵咬住之处,至于开拓心胸、不落言筌,大约还有一份诗的反抗在。”(224页)那只带着“自由的歌唱”与“诗的反抗”而冲天飞去的火鸟,就是陈建华心目中的诗人与学者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