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性总是和男性相关,而怀旧总带有女性气质?

文学和社会学之间保留着异常鲜明的学科界限。尽管文学社会学有一些拥趸
(虽然并不多)
,但文学批评家对社会学思想“大师们”的著作提不起兴趣。然而,最近的学科发展鼓励跨学科交流,这使得文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开始动摇。即使是最避世的文学作品,也会含蓄地影射一些它所试图超越的社会现实;同理,那些自称塑造了社会现实结构的文本,本身也受到了各种叙事、隐喻和修辞图式的影响。社会学理论也是一种再现行为,它借用了各种描述性词汇、分类体系、阐释方法和言说规则
(enunciative rules)
。通过解读这些再现的逻辑,我试图揭示性别寓言
(特别是那种充满了怀旧感的女性气质观)
在塑造现代社会学和批评思想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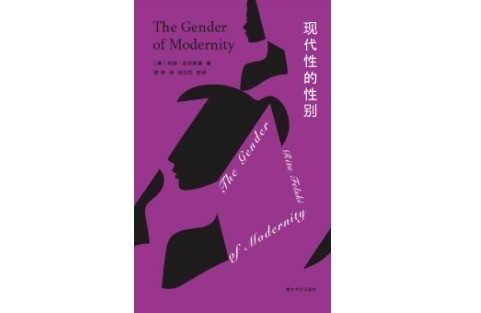
《现代性的性别》,作者: [美]芮塔·菲尔斯基,译者:陈琳 / 但汉松(校译),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社会学与现代性,
是互相决定的
在世纪之交,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了极大关注,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学正努力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希望发展成为一个不同的思想研究领域。伍尔夫·勒佩尼斯
(Wolf Lepenies)
在论及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时,将之视为文学和科学传统的不稳定混合体。他指出:“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文学和社会学就互相竞争,声称本学科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一个导向。”和当时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样,社会学家也以定义和记录时代根本特征为己任;只过了很短的时间,社会学的论述框架和术语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对人们对于现代的性质和意义的常识态度。社会科学的阐释范畴经由教育和媒体这样的机构,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塑造了我们对现代和性别许多习以为常的信仰。由此可见,主导某一特定知识形式的基本假设和盲点会远远超出它的学科起源,影响一个大得多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社会学的话语已经影响了我们想象现代的方式。
社会学通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现代学科,它在自由化的民主国家出现之前绝无可能存在。我认为,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是互相决定的关系;社会学是在其分析过程中帮助我们形成一种现实感,而不仅仅是分析某个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例如,很多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讨论何为现代,它其实与19世纪晚期文学中另类的现代形象既相关又不同;通过比较两者,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发现,看到那些划分历史时期的术语究竟是如何在特定话语中被建构,并被赋予意义的。正如现代概念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性质和内涵有所不同,女性形象的意义和隐喻关系在世纪末的各种话语中也历经变化。然而,除了审视这些差异,我也期望能够通过比较社会学和心理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设,在这两种话语域之间找寻相似性,探究它们相似的女性气质观
(即女性气质是未分化的前现代之物)
,因为它们都源自文化参考点和参照框架的共有联结。
在社会学努力确立其学科合法性的时期,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但在某些方面,他也颇为与众不同。他常被视为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没有荣膺那些来自体制的常见头衔。他在学术上和职业上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学术界泛滥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兼收并蓄,脱离了正统。齐美尔的兴趣远超出了社会学惯常的关注点,涉及了心理学、哲学、文化和艺术等各种话题。他看似随意地论及一些不相干的主题,如调情、废墟、把手、时尚、餐食、妓女、气味的社会学、陌生人和阿尔卑斯之行,梳理出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琐碎的现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塑造了个人经验和社会互动。戴维·弗里斯比
(David Frisby)
将齐美尔称为社会学的游荡者
(a sociological flâneur)
,因为他喜欢用印象主义的手法来勾画现代城市生活的经纬,而不是要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齐美尔坚持认为,社会现实已经不能再用整饬的总体性来把握,他想要去探索不稳定的,往往是碎片化的现代经验。这种倾向让他一生都饱受苛责,但也让他在当前文化理论的后现代潮流中魅力四射。如今的文化理论往往对总体性框架持有怀疑态度,而对现代社会的审美维度有着浓厚兴趣。近年来,学术界重新对齐美尔产生了巨大兴趣;他现在被赞誉为现代性的社会学家,或是超前的后现代或解构主义思想家。齐美尔似乎成了我们同时代的人。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188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1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他一生交友甚广,马克斯·韦伯等人都是他家中举办的沙龙的常客。
我对齐美尔作为社会理论家的独特性并不那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性别的一些重要论述,当然这种偏好很可能会导致对齐美尔复杂思想的某种暴力阐释。和很多早期社会学家不同,他写了大量关于女性和现代性的文字,尽管这些论述长期被评论家忽视,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如利特克·范·武赫特·泰森
(Lieteke van Vucht Tijssen)
所言,齐美尔是少数几个将性别关系作为现代化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的作家之一。齐美尔在论著中将社会学和哲学欲说还休的东西做了明确表达,从而让我们看清了许多把性别与现代性视为对立关系的假定。齐美尔发现,将男性和现代性等同起来的做法在他所处的文化中屡见不鲜,而他本人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于是,齐美尔在现有的象征和体制结构之外构想了一种真实的、自主的女性气质。因此,虽然他常被当作一个拒绝浪漫主义思想中那种乌托邦诱惑的理论家,但在其论著中女性事实上被视为怀旧欲望的明显对象。
我的观点是,这种将女性气质作为一种非异化、非碎片化的身份象征的渴望,构成了关于现代性本质的文化再现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在这些话语中,女人成为真正的起源点,是未受社会和象征体系影响的神秘指称;她成了反复出现在现代性中心的一个象征,象征着非时间性
(the atemporal)
和反社会性
(the asocial)
。因此,通过分析齐美尔的作品,我可以阐明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假定,它们认为现代性、异化和男性气质必须具有同一性,从黑格尔到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思想传统的深处,都能看到这种观点。在这种传统中,怀旧和女性气质在对神话般丰饶的再现中合二为一,以此为反衬的是另一种宏大叙事,它将男性气质的发展当成自我分裂和存在的失落。换句话说,怀旧并不代表一种犯有时代错误或边缘性的状态,而是现代性自我建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救赎性的母性身体构成了非历史的他者
(the ahistorical other)
及历史的他者
(the other of history)
,现代身份正是在其反面获得了定义。
浪漫主义笔下的女性:
带有救赎色彩的避难所
最初让我对齐美尔产生兴趣的,是齐美尔关于女性、性和爱的文集导言中的一句话。导言作者盖伊·奥克斯
(Guy Oakes)
指出,齐美尔将男性性格与现代文化的客体化本质视为如出一辙,因此,奥克斯认为,对齐美尔而言,“女性化其实就是去现代化”。奥克斯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了关于女性和现代世界的普遍看法。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非女性主义者,他们都常常认为真正的女性文化将会改变城市工业化社会的工具性和非人性化。保守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女性与非异化的自然和有机共同体之间存在所谓的紧密关系,保守派向往的是回到理想化的前现代,而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思想家来说,这样的女性化原则体现了一个乌托邦化的另类选项,它有别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和启蒙思想的专制。
卢梭的论著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他讲过如何以适合的方式塑造两性主体的心理和社会性,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性别差异观影响深远。他将女性气质划入自发性情感的真实之域,这种做法与浪漫主义对女性的刻画方式不谋而合,浪漫主义笔下的女性总是一个带有救赎色彩的避难所,保护人们不受现代文明的荼毒,而现代文明就意味着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以及城市环境的异化。因此,女性气质代表了人类从伊甸园堕落之前的状态,“那是在人类形成自我意识、与自然形成主客体关系之前的时代”。这种将女性气质进行情感擢升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时代的变音。19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化,使得时间经验和时间观念发生了改变,这导致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怀旧情绪,人们开始怀念那些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所威胁的传统。换言之,女人逐渐代表了一个更加自然化的过去,象征着那种业已失落的前工业时代生生不息的有机社会。
这种历史怀旧当然也可以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因为浪漫主义思想中总是频繁使用“大自然母亲”
(Mother Nature)
这一表述。从精神分析视角看,渴望逝去的黄金时代就是渴望回到“前俄狄浦斯”的心理完满的状态。母亲的身体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存在的完满,一种原初和谐的幻觉意象,与成人意识中的疏离和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精神分析学说倾向于认为这类幻想是人的本质构成,但它本身的形成显然受到了更大历史变革的影响,这种变化主要是指家庭关系的象征性再现和物质构成。在心理上渴求成为理想化母性,渴求前文化时代,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中家庭私有化功能的体现,因为母亲变成了专职照顾孩子的人;另一个因素则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日益显著,在此语境下出现了自我的新规范,它将女性定义为自然和情感的生物。“女性的时间”
(Women’s time)
并不是在线性的历史发展之外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循环式时间性,而是与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正是现代化带来了核心家庭的出现,并建立了母性的救赎之域。
这种浪漫主义女性观在整个19世纪都深得人心,不仅在文学中被反复提及,而且在科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各类文本中皆有体现,这些文本都试图去证明女性与前现代状态的紧密联系。在这种语境下,文明的发展和个体的发展
(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
被不断地拿来作类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文化中的性别再现模式。人们总是将女性和原始的前工业时代联系起来,与此相同的做法则是借助女性的母亲角色,将之和没有自我意识、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尚未社会化的婴儿勾连在一起。将女人与自然和传统视为对等,这早已在早期现代思想中屡见不鲜,而达尔文主义进化发展观的流行又让这种观点大放光彩,促使进取型的、不安现状的男性气质与有机的、未分化的女性气质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世纪后期,科学理论不断试图证明女性处于进化链上较低的位置,总是用儿童或是野蛮人的进化状态来与女性做比较。正如辛西娅·伊格尔·拉西特
(Cynthia Eagle Russett)
等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所言,女人被定义为尚未发育完备的人,和男性相比,她们是一种低级生物体,未能从普通原始的胚胎形态中充分分化。因此,女性气质究竟是代表了发展受限的原始状态,还是代表了未被现代社会的断裂和矛盾所影响的伊甸园式有机整体,这取决于作者到底是看重进步话语,还是更相信堕落的神话。
因此,将女性排除在历史之外,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历史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用文化兴衰的哲学元叙事来解释文明的发展。这样的叙事,体现了对历史终极意义和历史目的不容置喙的自信。19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迅猛且看似混乱的变化,这一切最终被解释为一种宏大的发展计划,而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就位于这个计划的中心位置。然而,关于遥远过去的田园意象反复出现,这说明人们对这些社会进程还抱有怀疑和矛盾的态度。如果说我们在体验现代性时感受到了强烈的创新、转瞬即逝和混乱的变化,那么它同时也滋生了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各种渴望。怀旧是对理想化过去的一种悼念,因此它成为一个有持续影响力的现代性主题:进步时代也是渴望的时代,人们渴望那个业已失去的想象中的伊甸园之境。

追溯“怀旧”的历史和词源,会带来一些有启发的洞见。该词最早作为一种疾病的名字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偶发的自杀倾向。迈克尔·罗斯指出,19世纪出现了大量的科学著作来研究这一令人费解的疾病,它们对该病的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都做了缜密考察。医生们一致认为,病人急切地想要返乡,同时也表现出急切回到过去某个重要时刻的渴望。病人切断了与当下时间的一切联系,遁避到对家庭和出生地的美好回忆中,并哀悼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怀旧之人通过逃离现实世界,表达了对过去的‘过度’依恋。这种逃离很微妙,病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患了病,而只是默默地渴望回到过去,直至死亡。”这种退行的毁灭欲望,是由现代社会的混乱所造成的,因为流动性的增强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大量人口离开家乡,失去了故土之根,从而也失去了与出生地和历史的自然延续性。
有些医生认为,女人不太容易产生怀旧情绪,因为她们的生活更静止,以家为主。换句话说,尽管女性作为母亲往往是怀旧的对象,但她们自己很少成为怀旧的主体。她们不渴望回到过去,因为她们就是过去;她们属于家庭领域,很少有无家可归之感,也不太会渴望那些逝去之物。当然,现在怀旧已经不再是一种病症,但是异化的现在与美好的过去之间仍然有着一根时间分割线,它仍然被投射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分野中。女人之所以被认为不那么容易怀旧,是因为她们不像男人,她们的生活更为静好,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相应地,母亲的家园对于那些逃离混乱、流动的现代生活的人来说,就是救赎的庇护所。女性气质继续成为一个能指,指向现代人不再拥有的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