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王家范(1938.9.22-2020.7.7)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刊于2013年7月14日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终身教授王家范于2020年7月7日凌晨五点在华山医院仙逝。《上海书评》特重刊对他的采访,缅怀王先生。
城镇化建设,现在是个热门话题。早在1983至1984年,费孝通先生先后发表过《小城镇,大问题》等三篇文章,有感于当时乡村企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主张中国现代化应走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可惜时局没有按费老预想的那样走去。大城市的扩张接近到了临界点,人们又想起了这个旧话题。费老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市镇,也包括乡镇。在明清乃至民国,江南市镇曾经相当繁荣,现在已成了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
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长期研究明清江南的市镇,他指出:明清江南市镇是从乡村经济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市镇是乡村经济的升华,衬托并支持着城市。如果没有了乡村经济,市镇不复有存在的意义。将来有一天,很可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这世界就会因单一而变得了无情趣。

王家范著《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2019)

王家范著《明清江南史丛稿》(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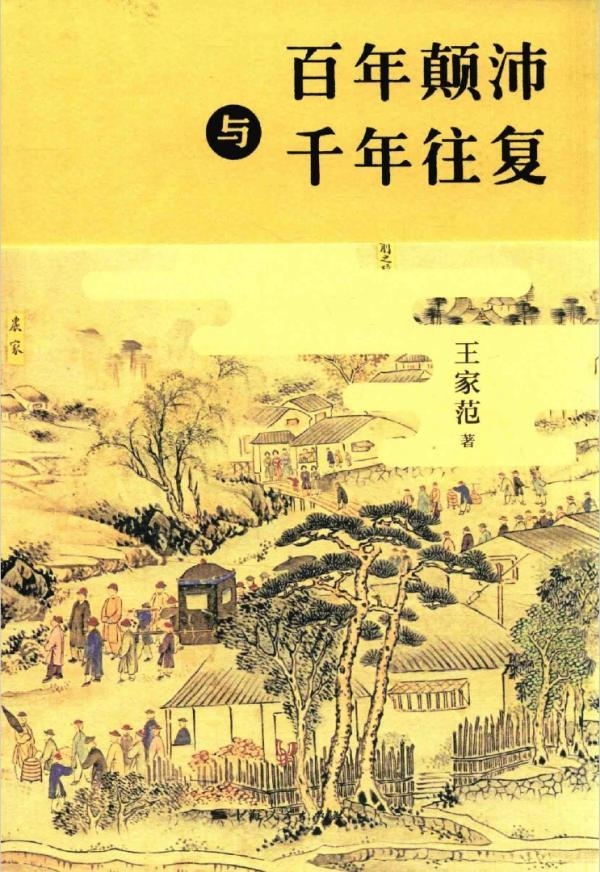
王家范著《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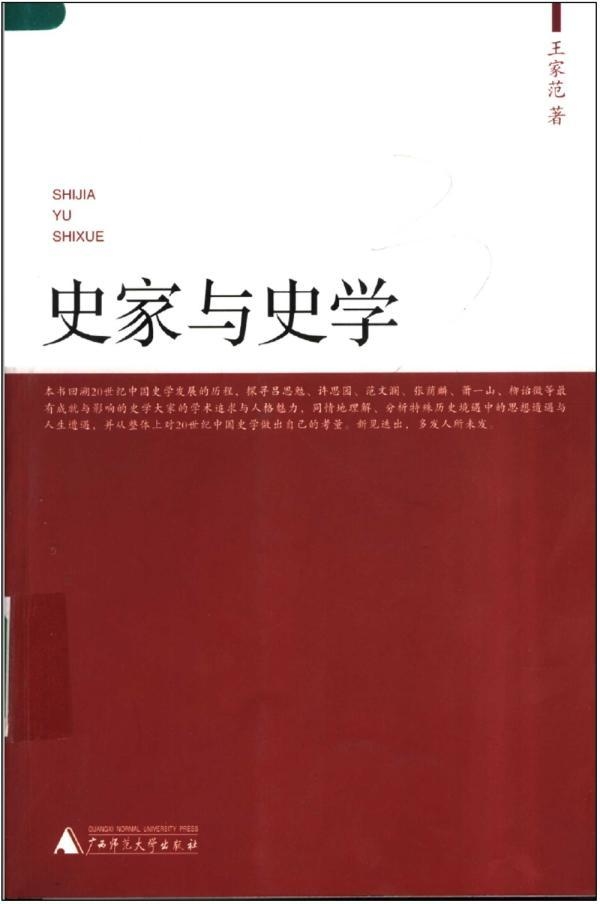
王家范著《史家与史学》(2007)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城镇化建设”,讨论十分热烈。想先请您就明清时代江南市镇,谈谈它是怎么来的?在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素还是政府有意识规划的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的起源,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还比较少,到南宋数量就多起来了。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其间,个别的镇有兴有衰,总体数量不断在增加。近代“海通”后,江南经济中心从苏州移向上海,有个大变化。概括地说,市镇不仅数量增多了,而且与城市的商贸联系也比此前大为增加。松江府各市镇(包括浦东)商贸一改西进的路线,纷纷东进;同样,杭嘉湖市镇北上东进,苏锡常市镇南下东进,均唯上海马首是瞻。总之,市镇网络格局与发展态势为之一变,也可以说是第二高峰期。今天来不及细谈了。
不少人并不知道,明清江南市镇,直到清末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以前,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那里仍然是按乡村的规矩来编制地域(都、图、里、保),且与四周乡村犬牙交错,镇区内也有农田与农民。所以,我若想简单地回答你第二问,用不怎么“学术”的话来表达:从宋以来,直到明清,市镇是体制外的产物。说深一点,它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农村商品经济、市场贸易发展的产物。市镇具有乡村商贸市场“中心地”的性质,衬托并支持着城市的生存与发展。
明清江南地方志(府志、县志)都是这样诠释的:郊外居民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乡村市场有草市、集市、乡市(大市)等多种层级。镇是乡村市场的最高一层,商业荟萃,店铺林立,比“大市”还大,周围乡民即约定俗成地认之为“镇”。例如清代以前,昆山大慈,原名“大市”,入清后才逐渐被称为“大慈镇”。陈墓一镇属两县(雍正后在江南各地,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吴县方志里称“镇”,昆山县方志里称“市”,因为商店、“市面”多数集中在上塘街。在明清直到我生活在乡下的年代:城是城,到昆山县城叫“进城”;镇是镇,四乡农民清晨到陈墓叫“上镇”,决不会混淆。这种城镇含混通称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倒可以追究一下。在学界,学者为着与府县城这样的政治性城市区分,特意用“市”来打头以示醒目,称之为“市镇”,而不用“城镇”这个词。只有县城所在地的“镇”好多是称“城厢镇”的。费老是知道这种历史原委的。为了从俗起见,他用了个“小城镇”的名称,顾名思义就是比“县城”级别低一等的“镇”,所以他说话里也包括了“乡镇”在内。
民国以后将“镇”与乡一起纳入行政区域系列,性质发生变异,往往是根据人口规模来机械划分城、乡与镇。清末规定人口满五万以上为镇,不满五万的为乡,标准显然太高;民国以后逐渐降低,一直降低到至少两千人以上(指非农业人口)。这种行政指令性的划分,往往与经济实况有差距。有些地方连乡带村地“圈进”冒报,数量遂急剧猛增,有的“镇中心”仅十来家商店,稀稀落落的,与乡市差不离,根本够上不“市镇”的水平,名不符实。这是行政操作难以避免的习弊,就像我们十多年以前做过的撤并乡镇,也是问题多多。这两段历史现在都需要检讨总结,以作前车之鉴。

王家范,2018年4月摄于扬州。
照您的说法,明清江南市镇主要是以经济功能出名的。能不能稍微具体地描述一下它们的功能?
王家范:在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发生得很早。市镇是由古老的草市、集市慢慢发展过来的,在它里头也仍保存着草市、集市的基因。它们因地制宜地自然产生,所以形态不一,没有完全相同的模样。在江南,有的街道仅一根扁担的宽度,有的宽至三米;有的一河一街,有的一河二街(上下塘),有的两河交织,呈十字街,有的东西南北还有小市(栅市)。以开设的商铺计,有的仅数十家,有的多至数百家、近千家。它们深入腹地(“乡脚”),有的广达二三十里,少的则仅是附近四五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附近乡民上镇出售农副产品以及购买日常用品的农村经济集散中心。
只要看一下市镇通常必具的商店种类,它们是:米店(或米行,兼收购代碾)、布店(绸缎店)、百货店、竹木店、面食点心店(面馆)、酒酱店、水果店、茶叶店、烟纸杂货店、南北货店、豆腐店、水鲜行、肉铺、药店、茶馆以及各类摊贩,还有手工业性质的榨油坊、橹店、铁匠铺和剃头店、浴堂、成衣铺等服务业。很明显,服务消费对象是附近的农民以及本镇的居民。如果附近乡村农民没有一定的消费需求与购买能力,这些商店很难生存得好。而消费的方式也带有乡村的特点,农民上街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包括鸡鸭禽蛋),在桥头、茶馆店前现卖换钱(形似草市),再买回所需物品回乡,甚至还通融用实物顶钱买回所需物品(我小时候还能看到农民用小布袋米去面馆换吃汤面)。小镇市面最热闹的就在农民上街的早晨两三个小时内,此后市面逐渐冷清下来,变成居民的零星购买(例如茶馆,第一批顾客多数都是乡民,晨光微曦,摇船上岸,或挑担而来,称之为吃头茶)。
有些“江南史”学者很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平凡的日常生活上,他们只对一些著名的大镇津津乐道。但我却要提醒:在多似星斗的中小市镇里,反映的恰恰是江南乡村经济的基本内涵。至少从宋以来(再往前资料更缺乏),江南农村经济发展的实态,打破了学界“概念世界”里的几条成见:在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耕地最少的江南农村,创造了可观的GDP(估算不容易,但在当时中国可能是最高的),没有出现绝对贫困,相反多数像是过着尚可温饱的“小康”生活,因此也不习惯于闹革命(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刘昶教授有文专门论证)。
史实证明,农民,包括租佃农、长短工,没有“概念世界”里想象的毫无消费购买能力,不参与商品经济。早在南宋年间嘉善魏塘镇,有历史记载曰:“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数十石;每一百石,(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方回《古今考续》)到明清,魏塘与枫泾(半属嘉善,半属华亭与后来的金山)都是同等有名的棉业市镇。江南农民靠密集劳动、精耕细作以及多种经营,使“马氏”恐惧的“人口灾难”变成经济红利,过的是节俭但并非不消费的日常生活。决不能低估普通人的经济开发理性,农民知道自己怎么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也知道市场是他们获取收益不可少的场所。
明清江南的市镇向称富庶,其棉、丝的输出量都远超其他地区,市场应该是很发达的,您能描述这个市场的特点吗?
王家范:是的。江南市镇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并不是我前面所说的老传统的市镇,而是以丝、棉为贸易重头戏的市镇,例如南浔、盛泽、乌镇、高桥、朱泾、枫泾、七宝、南翔、罗店、外冈等。它们都曾经因某种情势机遇,卷入跨区域的市场贸易浪潮中,充当了一回弄潮儿的角色。
江南地区农户种植棉花大约从宋元起开始成风气,而养蚕缫丝则以浙北各乡为盛,传统更久。湖州南宋时就有“湖丝遍天下”之说,而松江“布被天下”的局面真正呈现要到明代。为什么到明中叶起,这两项贸易变得更为兴旺?这是研究市镇的人不能不追究的问题。
答案是明确的,即来自于外部“大市场”的刺激。论丝与棉的销路,国内有两种大主顾:一种是官家需求。丝向来是由江南织造生产上贡皇室,后来改为发包给民间机户,也激活了本地民间的蚕桑缫丝产业。到明代,棉花与棉布也曾是政府派员收购的大宗物资,用于西北军事地带数量之大,已有专门研究报告揭出(西北商人频频出现在江南市镇便是明证)。另一种是官绅私家与豪富商贾的消费,包括边地的王公头领。民间普通地主商人也会有消费,但所占比例不大。明中叶起,国内经济显示三百年大王朝常有的中期繁荣,皇室与官绅感觉良好,白银货币化起了燃素的作用,公私消费上下都旺烧了一把火,世称“嘉隆万盛世”。
海外的研究揭开了另一类“大主顾”的面纱,那就是通过“东亚贸易圏”由海上销往欧洲。彼时的欧洲奉行重商主义,经济上升,奢靡风气渐盛,中国的茶、丝、棉、瓷器为其进口的四大宗。这种贸易即使在禁海的情况下通过走私贸易也从来没有断过。由此而带来的白银已经由弗兰克等人极其形容,而操闽语与粤语的商人,在丝、棉市镇的记载中往往被说成操“鸟语”的大商贾。白银从他们手里经市镇牙人、牙行中介,注入市场,运走一批又一批丝与棉,市场的繁荣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可以想见。
市场是个非常灵敏的经济调节器,农民的反应并不迟钝。丝、棉的生产原本是弥补江南重赋后收入锐减的“应急之策”。农副并进,多样种植,多种经营,一年忙到头,江南农民勤劳辛苦于此,生活不至非常贫困亦由此。这与北方有些地区(例如东北农民的“猫冬”)非常不一样。待到明中叶起,丝、棉市场大开,且能为他们赢得较粮食生产更高的收益,于是家家栽桑养蚕缫丝,户户植棉纺纱织布,机杼声日夜响彻乡间,甚至连镇上、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也参与进来。正是这种极其广泛的家庭手工业浪潮创造了“衣被天下”、“湖丝遍天下”、收不尽松江布、买不完嘉湖绸的“乡村经济奇迹”。反之,一旦国内或者海外贸易方面丝、棉销售不景气,农民也会及时调整,出现棉田改稻田、少养蚕少缫丝的经营“反转”现象。市镇的商业盛衰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坏休戚相关,只要看一下地方志,就不难得到深刻印象。

《王家范谈“长时段”看历史》,刊于2011年1月30日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除了经济因素,在传统中国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还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市镇自治形态?
王家范:从市镇出现来说,它并不是政府有计划设置的;但当它们出现并且显示出经济效益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自然会行动起来。首先想到的是财税,与此同时就是治安。巡检所、守汛(军事派出所)、务、场(税务分所)这些原有的机构,有的原在镇上,有的移到镇上;大的繁荣市镇甚至派出同知、通判、县丞坐镇(这种情况多见于清代)。但他们管辖的权限也仍然是这两大职能,辖治覆盖其周围的乡村,是县级行政深入农村的改良举措,但不插手干预市场经营门类及其业务。
自从北宋政府放弃“井田制”式的“土地国有”复古梦,土地的所有与民生经营自由放开,以后的王朝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经济运行过程(除国有的酒、盐专卖与织造局外),有形的手不去代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点像现在宣传的“政企分开”。对工商的管理仅限于征税,但对四乡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地摊概不征税。国家的财税大头在“田赋”(含役费),必须按定额上交中央,否则会降级甚至革职,依据是人口与田地数,这方面掌握难度大,花费的工夫也最多。一般市镇有相当数量的地主,他们的田赋征收仍按农村的规矩办(纳入都图系统)。而工商税,有过税与住税两类,法定是什一之税,收入主要归县府弥补田赋上交后行政费用的短缺。同知、通判、县丞坐镇的主要目的,也出于此。至于下属人员(包括临时工)对商贾借机敲诈勒索,虽有明禁也难遏止,事所难免,但较之田赋征收方面的腐败,乃属小巫耳。
明清市镇之间,或盛或衰,或兴或亡,因为全面连贯的动态考察在资料上有困难,目前系统的研究不充分。但有一些印象是比较醒目的: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一般市镇的寿命都很长(除非遭兵燹毁灭性打击)。少数大镇的繁华(如南浔、盛泽、乌镇、南翔)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地理位置处于周围丝、棉产地的交通中心固然是重要因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若干财力雄厚的富庶家族执其牛耳,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与政府有形之手无甚关联。
最后一个问题,牵涉中国历史走向与西方历史相异之处,不必去费力比附。在我看来,明清江南市镇还是相当自由的,彼时政府管得很少,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无论是戴毡帽的乡民,还是穿长衫的“先生”,街上相逢一笑,或许他们还是经常往来走动的亲戚,乡民认镇上人为干亲的也常有。生活很平常,人与人的感情靠得很近,没有城市里的那种疏离感与紧张感。我们曾经期待过有所谓“离乡不离土”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去说什么“现代化”,在数百年前,市镇倒是曾经实现过“离乡不离土”的情景,乡与镇是一种没有人为边界的联体结构。

王家范:《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2017年1月3日刊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看了一些研究动态,有把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称之为“城市化”的,也有称“城镇化”的?请问它与城市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算不算“城市化”,在学界有分歧。我这个出身于市镇的乡下人,对用西方“城市化”理论硬套中国古代历史向有反感。那些故意拔高的说法,计算那时“城市化”百分比有多高的数理统计,听来总觉得有几分滑稽。因为这明显脱离市镇的历史情景,更缺乏市镇生活的实际体验(至今所谓市镇旅游,多见不到土著的居民,怪不得年轻人没有印象)。我把这种高调讲给儿时一起嬉玩的伙伴听,他们还以为是城里人故意在笑话我们乡下人。
明清市镇的产生并不是由城市发动的,也不是由县级“城镇”向四周辐射形成的。有两种历史现象是对这种“理论先验主义”最有力的反驳:一是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例如围绕淀山湖、陈墓、周庄、商榻、黎里、芦墟、金泽、西岑等,出现了一连串市镇。二是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像南浔这样的情况在江浙地区均为常见,乌镇、盛泽、南翔、枫泾的经济实力都超过所在县级城市。
“城市化”在西方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人口、资源、科技、人才、企业、市场竞向城市密集,由密集效应产生的能量推动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城市的扩张都是通过吞并其周围的乡镇,促使其所占的“领土”越来越广大。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上海也经历过。例如今天新华路附近曾经是法华镇的中心地带。清乾隆、嘉庆最盛时,法华镇长街三里,工商云集,为上海城外首镇;晚清时,更有东、西镇之分。现在的新华路附近再寻觅不到一丝旧日乡镇踪影。如同“羊吃人”,城市吃掉了乡村和市镇,这就叫“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继“城市化”之后出现的城市带、城市圈,学界称之为“后城市化”或“反城市化”,对城市过度扩张的弊端已有纠偏去弊的意味。物极而必反,这个道理,中外相通,不能忽视。稍为注意一下西方的现状,就能发现在大城市、城市圈之外,他们并没有对乡村和市镇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许多国家农村与市镇的景象保存得令人羡慕。从电视、电影里经常可以看到欧美乡村市镇实景,那里没有高层住宅,二三层的古典乡村建筑错落有致,宅外绿茵芳草铺地,不远处耕地、丛林隐约可见,这与城市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画面相比,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生态美、居住美、生活美。城里人有兴致的,不妨“画饼充饥”,找些中外乡村市镇精美的摄影作品欣赏一番,以饱眼福。
现在我们再谈“城镇化”,在我看来不应属于“城市化”范畴,不应该是将城市化扩张模式推向广大乡村。它应该属于前此一直在期待努力实现中的“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自然会产生新的中心地,可称之为“新市镇”。它是经济(“市”)打头,而非政治(行政规划)开路,它是“镇”,而非“城”。新市镇情理所然地应该是农村经济新发展的自然结果,有四周的新农业(兼工商)营造出来的“经济圈”托底,富有本土特色的经济活力。这就决不是再度采取行政手段,将农村人口集中圈起来变成规划性质的“城镇”能完成的。总之,新市镇应该仍然是新的乡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有它自己的经济支撑点,有它主动向外扩展与输送自己经济能量的方式。
我所杞人忧天的是,如果所有乡村市镇都变成“城市”,将来有一天,可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这世界就会因单一而变得了无情趣。我并不甘心于让江南乡村与市镇变成我梦中的故乡,地下的遗存,只是留给历史学家去作怀古凭吊之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这场谈话就没有多大意思。
转自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