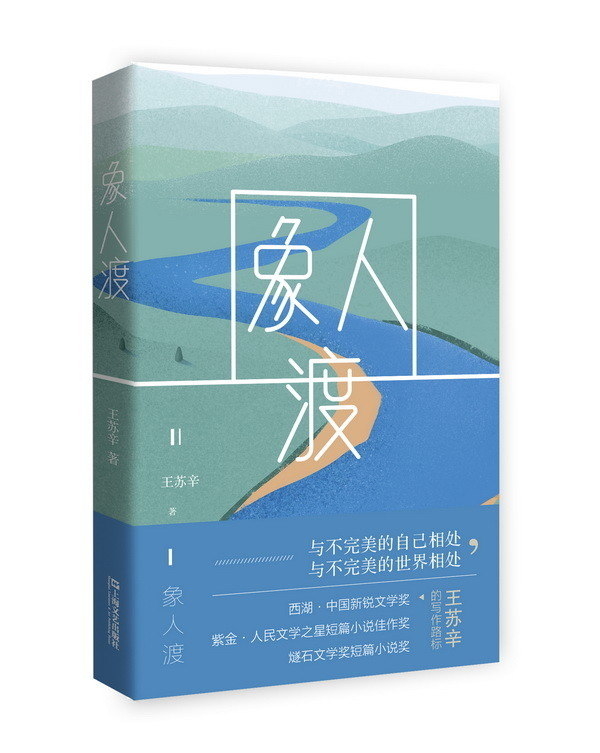王苏辛《象人渡》:直面内心对自己的各种限制
 2020-06-17
2020-06-17

“90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出生于1991年的作家王苏辛有自己的答案:
“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外表乖巧,在2020年之前没亲历过什么重大事件。很多人对‘90后’只有一种印象——看着非常统一,没什么值得说的个性。就像收割稻子一样,长得齐齐整整,都是金黄金黄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我想说,‘90后’的成长状态是非常隐忍的,是层层包裹的。”
隐忍地成长,王苏辛相信自己也是这样。从第一本小说集《白夜照相馆》到去年的《在平原》,再到最新中短篇小说集《象人渡》,她的关注与思考渐渐从完全虚构的世界转移到与自己及所处时代有关的具体问题,“十年前我会觉得,身边年轻人的事没什么可写的。我要写历史,写大时代,写福克纳式的小镇,那才是文学。但现在我知道当时的写作出自本能与冲动。当我关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我才稍微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写作状态。”
今年6月,《象人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小说集里,无论是《接下来去荒岛》中的“我”,《东国境线》里的郑东阳,《雍和宫》里的项奕,《象人》里的母亲,《二流小说家》里的A等等,都展开自己独特的精神之旅。这是一本有关青年人成长之困的书,也是一本伴随王苏辛自己成长的书。
“我一直相信,写作能够很清晰地作用于人的成长。尤其我现在写的小说,和我的关系非常密切。”王苏辛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最初写《白夜照相馆》时,小说对自己的成长也有作用,但整体来说依然是“写作的时候是写作,生活的时候是生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割裂,而现在的《象人渡》是一本从她的生命与生活里长出来的书。
“一个人刚刚开始写作时是在模仿别人,然后在模仿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仿佛是自己的声音,他跟着这个声音走,发现这依然不是自己的声音,那就继续走,直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个‘自己的声音’依然是阶段性的。”
当然,这样的过程并非没有犹疑和困惑。曾有读者直言,王苏辛的小说不再像《白夜照相馆》时期的那么好懂、好读了。
“我必须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人写小说是需要被认可的,他需要鼓掌的人。这些东西很世俗,但对于创作者而言又非常必要。”王苏辛毫不掩饰道,自己需要来自读者、专业评论家和同行的认可和同意,“但成长不会只是作品成长,判断力也会。我在意认可,但我也能渐渐判断什么样的说法可以和自己产生真正的对话,什么样的意见能够激发真正的火花。”
对她而言,新的困惑在于如何重新理解这个世界并作出表达。尤其在疫情之后,从前的许多认知都被打破,她充满了不适。
“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中国作家近年来受到的最大影响,就是你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关注的问题不再重要,甚至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她说,“ ‘90后’写作者中已经有不少人的作品呈现出成熟的面目,但具体到这些作品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代人的精神形象,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确立。说回我自己,具体到今后写什么,我还得继续思考。”
这样的坦率且坚定,对于王苏辛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

王苏辛
“有时‘想清楚再去做’其实是一个挺有问题的表现”
澎湃新闻:你会有年龄危机或困惑吗?今年元旦有一个热搜,叫“第一批‘90后’三十了”。
王苏辛:我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来自父母的压力,我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考虑他们的心情了。我会突然开始存钱,设定目标,甚至开始考虑婚姻的可能性……但其实更困惑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到现在这个年龄,我似乎也没有特别明白怎么生活是正确的。
澎湃新闻:“没有特别明白怎么生活是正确的”,这点我真有同感,它似乎是我们“90后”一代共有的精神困境了。路内在小说《雾行者》写到,九十年代的青年通过文学、音乐、电影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那在你的观察中,“90后”这一代通过什么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苏辛:我觉得每一代建立精神世界的方式可能都差不多,只是媒介不同。“90后”可能是还能享受比较自由的网络空间的最后一代,同时这个网络空间和“90后”的日常生活还没有那么密集的结合,我把这个还没有那么密集结合的时期定义为“微信出现以前”。就是在微信出现以前,大家还是有“网友”和“非网友”的区分。但有了微信之后,每个朋友都是网友。只要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他就成为了朋友圈中的一个头像,一个符号。
所以在建立精神世界上,我觉得“90后”一代会更复杂,这个复杂就在于你怎么能迅速地在变化中调整自己的思维。“90后”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像一个夹缝。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这个区间成长起来,见证了一段比较活泼,倾向于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时期,又逐渐经历了一个新问题不断出现的时期,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90后”被要求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所以,对我而言这个问题特别难答。一定程度上“90后”到三十岁了也还没有在精神上完全成熟。我前阵子有意识地去关注了一些更年轻的人,发现自己跟他们已经身处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更年轻一代关注的可能是更稍纵即逝的东西,而且他们在稍纵即逝中非常敏锐。我想,若干年后再看中国的“90后”,人们或许会觉得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成了某种标本,这个标本既有上一代人的理想色彩或者渴望,又有后一代人对稍纵即逝的留恋和捕捉。
澎湃新闻:确实,在这次疫情中,不少“90后”发现自己的世界观不断被刷新,而且新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困惑就消失了。在新小说集里,《接下来去荒岛》《东国境线》《雍和宫》等作品都有涉及这一代人对于工作选择的思考。我也隐约能从小说人物的心理、对话与行动选择感知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于“想做的事”“能做的事”“应该做的事”,你怎么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王苏辛:我觉得这几个事之间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有时距离有点远,但依然有关,就像很多编辑最早的愿望是成为写作者,很多策展人也是艺术家。
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旦工作了,就不能光了解自己,还得了解周围环境。不能说是随波逐流吧,但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顺势而为。因为有些机会真的只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才会出现,有些尝试也真的只在某一个时期可以毫无挂碍地去试。有年长的前辈告诉我,他们一开始做学术研究时都认为自己可以研究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后来发现要一点点地把研究范围缩小才可以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他还可以广泛尝试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不要害怕失败。因为,人生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让一个人做他只能做的事,如果还有一点点空间去做一点看起来稍微有点难或者说对自己是挑战和有些限制的事,是好事。
澎湃新闻:你这个回答让我想到《接下来去荒岛》,两个青年都身处长久的迷茫期,一个表达困惑的方式是不断“试错”,在行动中判断自己工作的前景,一个则是不想清楚就没有行动力。你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么?
王苏辛:其实我一直是不断“试错”的。但是这几年会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对自己擅长的事有了了解之后,会倾向于先去判断,再做决定。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有时“想清楚再去做”其实是一个挺有问题的表现。因为有的时候,想清楚恰恰是因为没有耐心。因为没有耐心,所以他不停地把这个事在脑子里演练。但一万遍的演练其实都不如他一步一步地直接进入这个事,然后在过程中发现与解决问题来得更清晰和准确。
澎湃新闻:在工作选择之外,小说里年轻人的社交关系也很耐人寻味。比如《接下来去荒岛》中的“我”在办公室沉默寡言,面对陌生人反而非常活跃,每一次活动结束后再删掉好友或退出小组;《雍和宫》中项奕和老友能在不同的APP上重遇,她反而更能适应这种“有距离”的交流。你对当下“人与人的关系”,有哪些思考?
王苏辛: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情,就是一方面渴望有很多朋友,一方面又不希望承担友情或者说其他情感中的责任。人一旦进入集体生活场景,就会发现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解决和分享,不只是那些快乐的部分,更多的是那些比较复杂和需要缠斗的东西。很多人都是既严格又不想承担责任,所以这两篇小说中会有这样的细节。我自己也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既想过陌生化的集体生活,又不喜欢欢聚之后的冷清状态,既不想进入他人的生活,也不希望他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就只想追求一个恒定的快乐感。只是我早已知道,不会再有这样的状态了,“快乐感”也在变得成熟,它成为一个徘徊在不同灰色地带的,需要我们不断辨认的东西。
澎湃新闻:我还发现,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写到了手机App,涉及地图、旅行、订餐、读书、交友等方方面面。这是巧合吗?
王苏辛: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个跟现代社会非常接近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平行世界。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高度现代化的东西。我会把一些现在看到的“苗头”进一步现代化,认为它可能在几年或十几年后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会有一点未来色彩。
但最根本的是,你提到的这几个关键词,确实是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青年的生活状态。手机导航、APP订餐,都已经不是新事物了。写作时我没办法回避这些东西。就像我做不到丢掉手机,丢掉“叫外卖”“叫车“这些行为方式甚至思维习惯,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些东西已经进入到这个时代,并且密切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写我所认为的当下时,它们的出现也是必然。
澎湃新闻:小说集的书名是《象人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王苏辛:有一个成语叫香象渡河,这本书的书名其实也跟这个成语有点关系。我自己理解的是,象人是一群看起来很巨大,很笨拙,但内心又非常敏锐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行动和精神状态有时会是不匹配的情况。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心情,就是有时你想明白了一个事,但等你把这个事落到行动上,它还会有一个很反复的过程。
所谓象人渡就是在讲述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自我的确立,对他的行为方式和状态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促成什么样的变化。
澎湃新闻:我在想,新小说集里的六篇小说其实都在对“人如何变化,如何成长”做出反思与探索。批评家张定浩曾对你的作品有这么一个评价:“王苏辛小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他也在对另外的人讲述自己的成长,同时这个小说跟她自己也是有关系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成长与小说的成长?
王苏辛:我的小说会随着我的内心变化和成长,它们是非常一致的。我也无比确信的是,一个人的写作和他的生活关系密切。这个密切不是说参与度上的密切,而是说写作会自然地帮助一个人厘清很多东西,这个东西本身是能够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这个能量也会渐渐地注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一个人的反省意识,自我教育的能力,很多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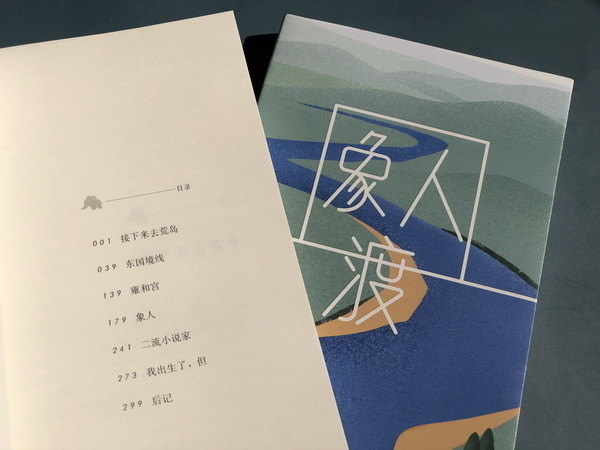
“我们这代人依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自己也好,为别人也好,确立一个特别清晰的轮廓”
澎湃新闻:谈到变化,从《白夜照相馆》到《在平原》,再到《象人渡》,你的写作风格与关注点有了很大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王苏辛:《白夜照相馆》当时被一些选刊转载,有不少人和我说今后可以就照着这个路子写。当然也不是说那篇小说就很好很成熟,而是说那样一个清晰的结构,那样一个鲜明的人物状态,那样一个现实与想象的交织,它能够被一些人所辨认。如果我能够顺着那条路去写,我未来的小说也可以是一个能够被许多人辨认的状态。理解《白夜照相馆》的小说世界,起码是比理解我后面写的《在平原》,包括现在的《象人渡》要容易。
我也一度设想过,要不就按照那个方式去写,但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白夜照相馆》是我在某一个时期的阶段性写作。尽管《在平原》《象人渡》也是我的阶段性写作,但它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写的小说和我的关系非常密切,它可以作用于我的成长。我写《白夜照相馆》时,它对我的成长当然也有作用,但是整体来说依然是“写作的时候是写作,生活的时候是生活”,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割裂。
当然,我也有挣扎,因为我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人写小说是需要被认可的,他需要鼓掌的人。这些东西很世俗,但对于创作者而言又非常必要。我曾经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写《在平原》时,会有一些人说“你这个东西比较难理解”、“小说应该是讲故事,而不是直接处理精神问题”,会有这样一些声音,但这种文学观或者阅读观的差异不值得去说,它们是由人的差异性决定的,与作品好坏无关。同样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在平原》才开始对我的小说有一些认同感,这种微妙的变化对我也是鼓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大。一个人刚刚开始写作时是在模仿别人,然后在模仿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仿佛是自己的声音,他跟着这个声音走,发现这依然不是自己的声音,那就继续走,直到找到了另一个仿佛是自己的声音。我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每一段变化都有递进,但都不是终点。
澎湃新闻:对你而言,“鼓掌的人”指的是谁?或者说,作家圈、评论圈、读者圈,你看重来自谁的认可?
王苏辛:一个人如果做了一件重要又很好的事,他自己是有感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进步,他不会只有作品进步,包括判断力在内的各方面都会进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首先自己的认可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人会比较舒展,对外界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在意。一个人对外界的声音过分在意,其实还是源于心虚,源于他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状态。
但我不能否认,大部分写作者,包括我,其实都是在独自攀岩,这样久了,他需要一些外围的声音,需要补充精神体力。人不只身体有体力,精神也有体力。如果一直独自跋涉,精神高度严肃,就很需要放松。所以我不否认我需要来自读者,来自专业评论家,来自同行的认可和同意,尤其需要能帮助我的批评和能真正鼓励我的同意。
每一个经过比较长时间写作的人,大抵都能判断什么样的说法可以和自己产生真正的对话,什么样的意见能够激发真正的火花。有的人批评得真狠啊,可是他说得有道理啊,那就要听。所以我很难说来自哪个群体的声音最重要,我只能说是来自哪个好的人。
澎湃新闻:对于来自外界的声音,你已经想得很明白了。那么现阶段你的写作困惑是什么?
王苏辛:对,现在新的困惑就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很多新问题来了。比如最基本的,自己的认识刷新了,小说如何跟着刷新?又或者说如果想写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杂的小说,它始终牵扯到很多不同的经验,源源不断地,那么这个经验怎么获取?
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可以留下一点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是那些稍纵即逝的信息、抖音视频等等,而是精神形象。一个时代的精神形象怎么确立?肯定是通过作品。我们现在可以说,像“70后”作者也好,90年代中国也好,21世纪初中国也好,可能都有这么一部两部小说或者文艺作品,我们是能想起来的。
但是我们这代人依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自己也好,为别人也好,确立一个特别清晰的轮廓——有关“我们这代人(哪怕是一部分)究竟是怎么想问题的”。我这几年一直在尝试这个事情,我相信一代人精神变化的过程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作品。
澎湃新闻:除了写作者,你也是一位文学编辑。你对眼下的文学生态有什么样的评价?
王苏辛:整体而言,我觉得目前的文学生态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年轻作家密集出书的繁荣时期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我们的主要文学大奖,既是颁给作品,也是颁给人,会考虑作家的整体作品质量,整体文学成就。那些突然有一篇两篇写得不错的作家,可能很难经常得奖,或者说很难得奖。同时,一些名家会反复出现,一般的新人很难挤进这个队伍。
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醒年轻的写作者:作品不仅要好,还要很重要,要能提供自己真正的洞见,以至于不得不被承认,不能被忽视。我相信如果一个年轻作家,有这样一个作品出现,还是会被人看到的。只是在此之前,他可能要经历一个很难的过程,不止是写好作品,还有端正心态。
澎湃新闻:就创作而言,你认为“90后”这代是拥有了更多自由,还是更多限制?
王苏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实话,我肯定是认为有了很多的限制。这个限制不绝对是外在的,也有一些源于自己。自由意识看起来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很普及,但回到写作,比如我就会很困惑,有时看一些小说,我完全看不出来作者跟我是差不多的年龄。无论是文学观、叙事方法还是追寻的意义,他都像一个从几十年前走过来的人,但他却放着一个简介,说自己是“90后”作家。
当然,这不排除是价值观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无论我们写哪个时代的东西,使用哪种语言,最终让作品立起来的,还是作者的洞见。如果没有洞见,无论是写怎样的历史,怎样的时代,它都是空壳,都是一种装饰。
如果一个人真是像几十年前的人那样认识世界,那么我倾向于认为他把自己限制住了,他把自己限制在了某个历史时空,某种文学审美,他没有把自己放在2020年,起码没有把自己放在21世纪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直面内心对自己的各种限制。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虽然有很多精神意义上的远行的机会,但我们的思想有时依然停留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表现得很乖巧,但是我们的内心要有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