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陈更多只适用于局部而不是作品的整体——看王强的《我们的时代》


老实说,现在要拿起一部长达百万字且几乎可以预判文学品质未必一流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来阅读,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而支撑我这种勇气和耐心的动力完全来自好奇:一是《我们的时代》这个书名,它无疑更像一部专题论著而非小说;二是由于作品将这个“时代”的区间限定在1990-2018,这恰是本人十分有兴趣“阅读”的一个时段;三是作者王强本人在这个区间内用七年的时间从国内电脑公司的底层员工一路飙升为IT行业在华机构的高管,此后又在互联网领域创业并涉足风投、战略咨询等行当,且十几年前还因其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而挤身畅销书作者之列,对这个时代有如此亲历者的 “自述”也是驱动我好奇心的重要诱因。
在王强看来:“1990-2018年,是中国近百年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时期”,“无论美好与无奈、狂欢与落寞、收获与付出,这都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时代”。而在我这个年龄段人的眼中,“我们的时代”无疑还要上溯十余年,如果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所坚定的对外开放,王强们又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好在历史没有假设,正是因为三中全会、小平南巡两座历史丰碑的巍巍然,王强笔下那“我们的时代”画卷才得以徐徐展开。作品以IT浪潮为背景,展示了以裴庆华、萧闯、谢航三位60后同窗为代表的创业者逐梦历程,他们分别作为本土精英、外企精英和野蛮生长创业者的代表,并上溯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谭启章,下延至企业家二代谭媛、80后向翊飞、85后司睿宁等众多怀揣创业梦想的各式人物。在这些个人人怀揣“老板梦”的创业者群体中,成功者的笑容,失意者的叹息,不同的遭遇、众多的切面共同烘托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无论是1992年小平南巡、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北京奥运这些历史性的大事件,以及电视剧《渴望》热播、汪国真诗集走红、走谈式恋爱等一代人的共同生活及情感经历都在作品中得以呈现。这一切无不忠实地记录着那个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客观地说,王强写作《我们的时代》,既企望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又不得不借助商战这个自己熟悉的形态来实现这样的企望,这无异于给自己设置了两道难题:一是王强企望记录的这个时代近在眼前,所谓远时代易写而近时代难,这几乎是所有写作者的通识;二是大多商战小说的通病就是只见商不见人。由于第一道难题之难远大于第二道,暂且按下不表,不妨先从第二道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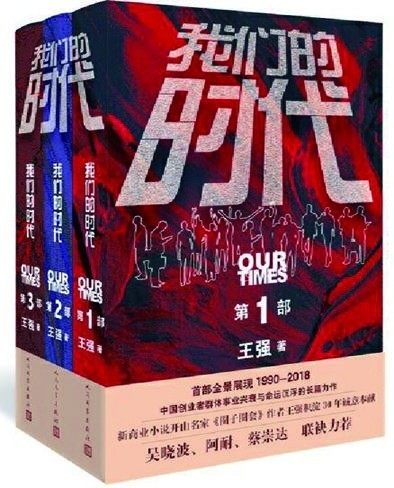
还是客观地说,由于王强自己既有参与商战的经历又有小说写作的历练,因而在处理“商”与“人”关系时的表现总体上还是可以称得上差强人意。尽管作品中依然有不少“商”的赘述,但“人”的形象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的形象还是立得住、站得起的。比如裴庆华、萧闯、谢航这三个60后同窗创业者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分寸得体。能做到这样其实也是颇需费一番思量与拿捏的。三个同窗间既有曾经的热恋也是彼此的好友,他们在同一行业中共同怀揣着自己的创业梦想,这样的关系在作品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落入不是大家相互帮衬一团和气就是彼此厮杀得你死我活、你红我黑的套路。但在王强的笔下,他显然对此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作品中对这三位同窗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及性格特点等都有足够的铺垫与交代,因而在此后各自职业生涯中各人特有的行为特点及差异自然地呈现出来,在彼此的关系上既有剧烈的冲突又不乏本能念着旧情的节制,整体看上去还是合情合理、收放有度。再比如在谭启章、裴庆华、萧闯、谢航、谭媛、向翊飞、司睿宁这些不同代际创业者间的行为方式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不同表现也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种分寸感的拿捏显然都是用了心下了力的。因此,尽管作品中出场人物不少,但一些主要或重要人物都会因其自己明显的标识性而在读者端留下记忆,在商战小说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
回过头再来说所谓“远时代易写而近时代难”这个难题。这一易一难,其中缘由本也不复杂。所谓“远时代易写”无非是因为经过时间海洋的淘洗,一些在当时还模糊不清的轮廓得以清晰的呈现,一些当时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麻烦变得不那么敏感或不那么重要,一些当时是非不明的评价被实践给出了答案……反过来所谓“近时代难”当然同样就是难在对上述问题的如何处理。《我们的时代》意在记录1990-2018这个风云的时代,这距离王强写作的时间真的是太近了,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长是近在眼前,清晰可见,短则在江山人事依旧,拉不开距离,必然少了些沉淀消化思考的时间。应该说,因其自己就是参与者,王强对这个时代并不缺少感性的认识,他在作品的“后记”中对此有一段很具体的评价:“如果不考虑因国企改制而失业下岗的人群,1990年代是很美好的,如果不考虑在金融危机中与国进民退中蒙受损失的人群,2000年代是很美好的;如果不考虑还有生活在贫困地区没有脱贫的人群,2010年代是很美好的。”都是“很美好的”但都有“如果不考虑”这个前置条件;如果“考虑”了,答案又会如何?其实即使没有这些个“如果不考虑”,评价这个时代是否美好的标识除了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外,是否也需要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呢?诸如时代精神、时代内涵、时代风骨、时代气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时间的淘洗、需要作者的理性……这也是所谓“写近时代难”的原因所在。我武断地以为,王强在写作《我们的时代》时,显然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因而表现在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基本上就只能是IT业“流水账”式的记录。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水账”不过只是一种比喻,由于缺少对一个时代形而上的理解但又想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流水账”式写作就不失为一种选择了。但说到底,真实而深刻地记录反映一个时代,重要的绝对不在于篇幅的长短、事物的巨细而在于能否抓住时代精神与时代魂。道理很简单,一个时代的全貌根本就无从用事件来穷尽,而只有时代的精神与灵魂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浓缩与精华。
从《圈子圈套》到《我们的时代》都是三部曲式结构,为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王强写作的毅力,但我还是要冒昧地建议他下一部的写作能多考虑些提炼与概括,铺陈恐怕更多地只适用于作品的某个局部而不是整体。在《我们的时代》中,同质性的写作、缺少节制的铺陈的确还有不少,如果能够加以必要的剪裁和提炼,作品或许会更有力量,作者那种 “往回看的目的在于朝前走”的写作初衷也会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展现。
作者:潘凯雄(知名文艺评论家)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卫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