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思想史家琼斯:英国工业革命之下的零工、工人与贫穷

盖瑞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是杰出的政治与经济思想史、经济生活与活动史家,曾一度执教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现任伦敦玛丽王后大学观念史教授。他率先发起以史学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执掌剑桥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期间,他与关注早期现代思想史的剑桥学人并肩培养了一代侧重十八至二十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家。他所著《遗弃的伦敦》(Outcast London)、《阶级的语言》(Languages of Class)、《贫穷的终结?》(An End to Poverty?)以不同维度探索了工人阶级备受忽略的历史经历。琼斯读史阅世之余,曾编辑《新左派评论》,合作创立了《历史工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较早并广泛地参与了西方新左派社会运动,在公共舆论界反响强烈。
近期哈佛大学政治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李汉松专访了琼斯教授,在这篇访谈中,琼斯回顾了个人从学生时代起的政治活动与思想变迁,回应了一系列关于劳工史与思想史研究范式的问题,并对时下的政治与经济难题提出己见。

盖瑞斯·斯特德曼·琼斯
您最初撰写《遗弃的伦敦》,关注的是伦敦的“零工”(casual labour)群体。您的经济史学方法是如何形成的?
琼斯:首先,读中学六年级(访者注:即第十二年级)时,一位名叫菲利普·惠廷(Philip Whitting)的历史老师对我启发良多。他并非现代史家,起先专攻拜占庭史。但他对其他史学时段和领域涉猎极广,讲授历史犹如变魔法一般。与此同时,我父亲作为一位英国文学教师,鼓励我大量阅读18-19世纪小说,尤其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也许正因如此,19世纪最终成了我的史学专长。
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时,您是刻意择取经济信号和主题——济贫院、赌博场、城乡经济、童工问题?还是如罗斯柴尔德教授(Emma Rothschild)所说,对照19世纪的英国工业社会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城市?抑或是纯粹着迷于文学,后来有意无意之间,才与经济思想会通?
琼斯:我的直觉是,阅读文学与研究经济之间的纽结在于探索这些人物角色所处的社会百态。直到后来读大学时,我才涉猎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在牛津林肯学院,我选修了数门不同的经济史课,尤其着迷于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后来在博士研究阶段,我转去以实证社会科学著称的牛津纳菲尔德学院。参与纳菲尔德学院的研讨会使我接触到了最前沿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辩论。但一直以来,我都多一半是历史学家,少一半是社会科学家。但最早时,我的学术兴趣还另有一个源头:一位出色的法文老师向我传授了一套清晰的现代主义文学观,谆谆教诲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鉴赏哪些作品。于是,高中毕业后,我怀着对19世纪法国小说的饱满激情——如司汤达(Stendhal)和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来到巴黎,度过了现在颇为时兴的“间歇年”。1960至1961年,我在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工作。当时,我自然而然地受到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法国社会主义与存在主义思想家吸引。回到牛津后,我又满怀热情地阅读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品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历史理论。但我也在读法国史学,尤其以年鉴学派(Annales)为重。写作《遗弃的伦敦》最初的灵感来源之一,即是路易·谢瓦列(Louis Chevalier)1958年出版的《劳工阶级与危险阶级》(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其中探讨了19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巴黎社会底层的穷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罪犯”这个问题模棱两可的认知。在牛津,除了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外,我另一个兴趣点是“第三世界”与“去殖民化国家”等政治问题。我记得当时受到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启发甚多。作为《埃希丝》(Isis)的编辑之一,我当时主要撰写有关第三世界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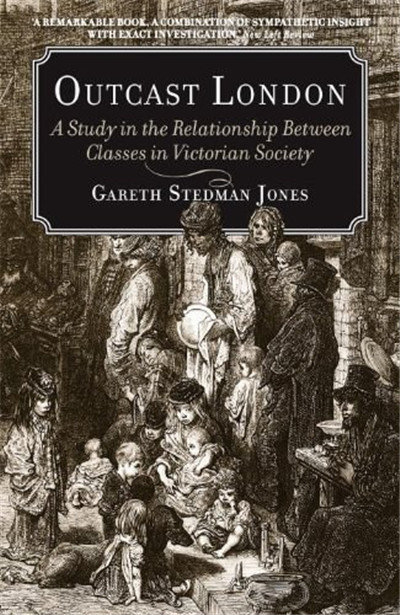
《遗弃的伦敦》
您指的是牛津学生刊物《埃希丝》?好像至今仍然刊印。
琼斯:是的,这部刊物因泰晤士河流经牛津这一段的别称“埃希丝河”(Isis River)得名。就这样,在研究第三世界时,我最早对“零工”发生兴趣——现在人称之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包括缺乏工作稳定性和技术含量的全部劳工领域。第三世界城市充斥着这种零工,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就此,我开始思考: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零工经济又是如何运行的?诸多想法一经汇流,便形成了我的研究课题——19世纪的伦敦。甚至可以说,不是我选了题目,而是题目选了我。
起初,我着眼于民众自由主义(popular liberalism):它究竟有何含义?又何以失败?顺着这一思路,我起初将论文题目选在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谓“自助”(self-help)这一意识形态。但当我潜入原始史料后,我愈发体会到的却是“自助”的对立面:于各种贫困而言,“自助”无过乎一种抽象而不切实际的补救。但通过阅读“自助”方面的史料,我愈加深切地理解了19世纪伦敦经济真正面临的诸多困境。那时,伦敦史研究严重匮乏,但绝非乏善足陈。原因是,大多数经济、社会与政治史家都热切地投身于工业革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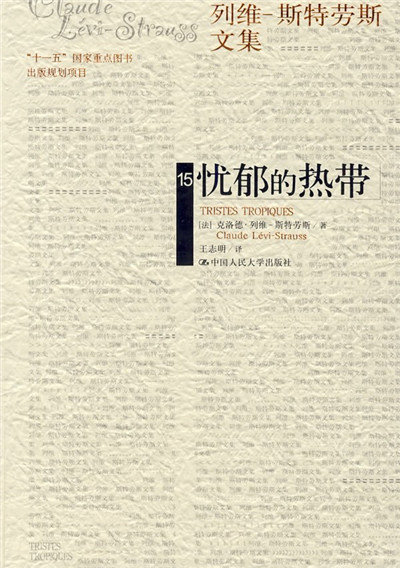
《忧郁的热带》
传统的工业革命史关注英国北部的大型工业城市,忽略了南方的经济,包括伦敦。
琼斯:正是如此。既然伦敦当时缺少大工厂工业,可想而知,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所以态度冷漠。对我而言,能作为先行者,开垦一块当代研究不足的学术处女地,可谓是绝佳的良机。这便是我写作《遗弃的伦敦》最初的语境和框架。
您关注的这部分零工经济是许多人眼中的“残滓经济” (residuum)。对这些零工而言,上有正经的工人阶级,下有所谓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夹在其中,近乎于现代经济学中“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概念的前身。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关注这部分貌似无力提升政治意识的人群。您试图揭示的是:贫困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这一流动性极强的劳工群体不容忽视。
琼斯:的确如此。当时作为青年历史学家,我收获颇丰,还得益于另外一点:虽然现代历史学对历史上的零工经济研究甚少,但维多利亚时代却已有不少令人惊喜的成果,如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报告。除此之外,最大的资料库来源于伦敦各城区医疗健康官(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的年度报告。他们在伦敦各个经济区,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当地的就业与卫生状况。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经历了1956年苏伊士远征后,我逐渐左倾。牛津毕业前夕,我颇受新左派吸引,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工作了数年,期间写了不少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各位大历史学家的文章。
我正要问您《遗弃的伦敦》与《阶级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说后者是对于前者的一种负面的反应,或正面的反补,都不甚准确。《遗弃的伦敦》揭示的是经济组织、社会成分等方面的新知,譬如,劳工和失业率如何随着季节变化;而《阶级的语言》更像是对某种历史经济主义的批判,比如“奥尔德姆的工业机器更发达,所以工人的革命意识也一定比北安普顿和南希尔兹的更为先进”之类的论调。
琼斯:你说得对,《阶级的语言》针对的批判对象并非是《遗弃的伦敦》。重拾旧著,我仍对当时揭示的伦敦经济结构、季节性框架、就业率与失业率的不同波动形式等,感到基本满意。所以,你刚才提到《遗弃的伦敦》中这些关于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分的史学分析,比如说对于这些零工们生活结构的描述,我认为时至今日也是颇为中肯的经济学洞见。因此,我也继续引用其中的结论,并从中汲取经验。《阶级的语言》更多是在修正一种经济决定论。你举的例子很切中要害:不能仅仅因为蒸汽率先来到奥尔德姆,就说在这里操作大机器的工人一定比北安普顿的鞋匠们更激进。那么该如何判断呢?我认为应该分析他们的政治语言、议程与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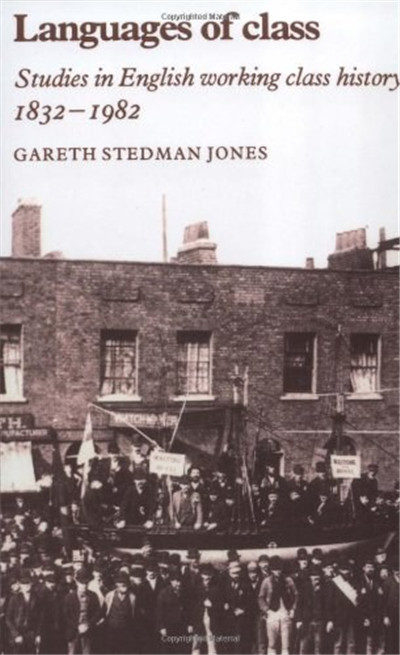
《阶级的语言》
现在反思这两部书,您认为经济组织与语言表述这两个维度之间的连接点和转折点在哪里?
琼斯:这涉及到《阶级的语言》的另一批判对象:一种过度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浪漫主义英雄化工人阶级的生活(如汤普森那样)。我试图说明:如果1820年代至1840年代是“工人阶级的缔造”(汤普森著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那么1850年后则有一次“工人阶级的再造”(re-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而且这一次产生了更加保守主义化的工人阶级自我认知观。而这种更保守主义的工人阶级身份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甚至体现于1950年代英国工党的某些主流态度。
“语言”是许多哲学与历史思潮惯用,甚至是擅用、滥用的概念范畴与分析范式。当您谈“阶级的语言”时,对您而言,何谓“语言”?而对于思想史,语言又意味着什么?
琼斯:于我而言,语言意味着论述与辩论。我主要受法国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主义者们坚持遵循一种他们称为“问题域”(problématique)的认知观念。而巴特和他的传人们也掌握了一种类似的概念:“共时性交流”,由此展开种种论述形式,并为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提供媒介与架构。在《遗弃的伦敦》中,我便应用了类似的概念,分析人们在观察理解、评议臧否“零工”问题时,所用的语言如何从“士气挫败”(demoralisation,访者注:指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向“风气退败”(degeneration,访者注:指工作积极性降低之后,零工作为社会群体的道德品质败坏)转变。“士气挫败”指零工作为个体的无知,以及他们对“自助式自由主义”信条有意的蔑视。相比之下,“风气退败”则从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出发,认定这一部分人群有某种生理缺陷。这些是我主要的灵感来源。
或许,《贫穷的终结?》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思考政治思想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以及您和斯金纳教授的分工和统一。首先,“贫穷思想史”中贯穿着一个共和主义语境。在十八世纪,主流思想家认定,共和制只适合小型国家。但美国、法国革命迫使人们思索:大型欧美国家是否也能成功实现共和?是或不是,这个答案又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扶贫、脱贫的态度?这便引出了一个政治语境。其中,潘恩与孔多塞试图证明:使用全新的方法解决贫困是完全有可能的。请问:在政治经济思想史中,“探索共和”和“思考贫穷”之间有何关系?
琼斯:正如罗斯柴尔德教授论证的那样,潘恩善用斯密经济理论的方式之一,便是将欧洲与他最熟悉的美国语境相互对接。当时有一种想法,尤受激进知识分子青睐:美国也许能为欧洲大陆的未来提供一种新模式。在此之前,确如你所说,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共和制度与小型城邦匹配,不适用于大型欧洲国家。具体而言,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尽可比,因为美国既无地主权贵阶级,亦无欧式财政制度。而潘恩的激进之处在于:他通过思索美式共和,完全可以想象出我们现在称为“社会保险”的保障制度。这一点可以与孔多塞的洞见合二为一——通过某种“社会数学”(Mathe matique sociale),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基于大量的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统计数据,创设出一套“社会保险制度”。这在英国尤其适用,因为英国已有自己的“济贫法案”(Poor Laws)。

潘恩
这多少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济贫法?
琼斯:正是。英国“济贫法案”以降,救济之权已成某种共识。基于这一观念,许多后世的社会改革议案都不标新立异,而是自我标榜为济贫传统之延续,以便更易得到社会的接受。在19世纪,许多人紧密团结在恶名昭著的1834年“新济贫法”(New Poor Law)旗帜下,阻挠劳苦大众申请救济金,理由是,只有济贫院(workhouse)内部才有义务提供救济扶持。但是截止到19世纪末,救济愈渐慷慨,而且可以直接发放入户。在爱德华时代,屡次重大社会改革实现了养老金、疾病与失业保险金。我写这部书的政治动机之一便是挑战一种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成见,即在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内反对济贫,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青睐的经济政策。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盛行的时代,您试图证明亚当·斯密反倒是“济贫经济”的鼻祖?或者保险一点说,起码在贫穷问题上,您试图将斯密从一种最简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态度中分离出来?
琼斯:是的,我着力论证出,最早阅读斯密的思想家都是激进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
您提到了孔多塞的“社会数学”。当时牛顿、莱布尼兹在微积分领域的创造已然成熟,加之笛卡尔、克拉默、高斯等人对于线性方程探索,以及费马、帕斯卡、惠更斯的初步概率论,形成了一个大环境,使得精算会计学成为可能。可否说,系统性设计福利政策的历史是现代社会应用科学改造政治最辉煌的一笔?
琼斯:不错,这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革命之一。
既然如此,您如何理解科学史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史的关系?
琼斯:那个历史时代不乏巨大的社会科学建树。首先,你研究过英国弃婴史,依据的史料大约便是伦敦各教会牧区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开始统计的人口死亡数据。但很明显,他们这样做,起初并非是为了有助于精算,而是准备迎接下一次大瘟疫到来。先不谈中世纪末的致命疫疾,单说1665年至1666年的瘟疫,据一些学者预测,死亡人数高达十万人——这相当于伦敦市当时总人口的25%之多。病死率一度飙升,这在当时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但18世纪中叶以降,陆续出现了人寿预测。人们逐渐发现了统计学的惊人潜能:统计学可以为政治家、各级行政人员,以及普通大众们打开全新的视窗,探知不一样的世界现实。1801年,英国做了首次人口普查。这段时期,“公平人寿”(The Equitable Life)等最早一批保险公司应运而生。在那之前,人们对于“盈利”与“亏损”的认知局限于抽奖、赌场时“赢钱”和“输钱”的概念。若说人为计算出“运气”和“偶然性”,当时可谓天方夜谭。但现代概率学的理论框架使在一定限度内控制偶然性成为可能。所以我认为,这是18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保险公司才可以承诺:今朝富贵,明晚也不必破产。孔多塞与同事们正是运用了这些统计学的洞见,才建构出了新型国家政策的数学基础,继而发展成为社会保险制度。
起初,这仅停留在一种抽象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进入到1780年代,法国因为援助美国独立战争,濒临破产,统计学成了紧迫的政治需要。一夜之间,孔多塞等数学家都成了国家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领军人。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些论点和论证继续展开。潘恩并非数学家,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数学界的发展对于变革中的政治有着何其重大的意义。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抚育金(child maintenance)、养老金(old-age pension),以求消除大多数普通家庭在福利与穷困之间剧烈动荡、起落摇摆的威胁。他意识到,只有通过精确统计,才能确保人们不再受暴富与绝望两极之间不断转变的折磨。其中还蕴含着一个远见:平日的合理投资可以对冲,甚至抵消危机时期不确定因素对于家庭生活带来的剧烈震荡。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展。它诞生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并且营造了一种氛围,引来了19世纪形形色色的“济贫改革法案”,最终启发了由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勾勒出的20世纪福利国家政策。

孔多塞
人们曾认为潘恩有多么的具有革命性,甚至多么的危险!仅在1792至1793年间,英国和威尔士便有超过300个乡村和城镇焚烧了潘恩肖像。切齿之恨,可见一斑。但是到19世纪,这些社会改革观念都逐渐合理化了,甚至得到了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保守派人士的接纳——当然,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因为只有实现了温和的改良,才能镇压激进的革命。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80年间的社会福利改革即是一例。目前,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向北部的蓝领城市伸出了橄榄枝,摇身一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甚至为了撒钱搞福利政策,炒了自己一向倚赖的财政大臣。这是否是一种历史规律?
琼斯:精明的保守主义者发现一些观念有利用价值,便将之从激进的政治议程中割离出来,再赋予它们一种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含义。这似乎正是鲍里斯·约翰逊目前的所作所为。俾斯麦当然是个绝佳的例子。他延续着威权主义的政治态度,采纳了一些社会改革项目,用以削减社会民主主义的潜在威胁。这是否是个通用的模型?我不完全确定。但你说得不错,这一策略在不少历史情境中都曾得以实践应用。
孔多塞关心的不仅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还有国际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当然,这事关许多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热衷探讨的“奢侈与商贸”之争、“穷国与富国”之争。这段经济思想史如何帮助我们思考当前的全球贫困问题,最终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琼斯:鉴于十九世纪后的那一段帝国主义史,这一目标既富于挑战,也充满可能性。帝国主义固然招人憎恶,但矛盾的是,它在历史上的确激发了一些受压迫国家(subject state)人民重获新生,走向富强的愿望。显然,若说完全消灭世界贫困,听上去既抽象,也乌托邦主义。但不代表没有循序渐进的方法。不论如何,消灭国际贫富差距应当是我们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