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庞贝到中山古国,就这样一路走来

原文 :《就这样一路走来》
作者 |同济大学 陈家琪
图片 |网络
庞贝古城:毁于自然
久闻庞贝古城遗址大名,去年秋天去到了那里。

周围的一切显然都在努力维持原样,几乎看不见现代建筑。导游告诉我们,庞贝古城不过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人口,但大型的浴场有五个,可坐上千人的大剧场一个,小剧场两个,现在已经用数字排列开来的商店有几十家。此外,还有两家妓院。所有马路(真正的马行之路)上相隔不远就有一道道用石块铺就的“斑马线”,石块之间有马车过往的痕迹。
导游站在一条马路上说:这就是庞贝古城的南京路。看着两边的住家和商铺,可想见当年的繁盛。还有三处人型骨架,或站立,或侧卧,据说都还保持着当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将古城掩埋时的神情与姿态。一座城和城里的所有生命瞬间化为乌有,让人想到了比原子弹更为可怕的自然威力。远远望着静静的维苏威火山,对这种自然的威力,除了表示敬畏,还能怎样?

这可与原子弹不一样,尽管都是毁灭一座城市,但一个是人的事,另一个则是自然的事。自然之事自然有自然之理。也许我们可以联想到罗马帝国中后期的扩张、掠夺与奢华、腐败,但人与天之间真的存在着这样的因果报应关系吗?看着阿波罗和宙斯两座神殿的遗址,也想到了在人的敬拜之心后面所隐藏着的功利成分。什么才算纯正的信仰?在我们日趋严重的对奢华与欲望的追求中,来到庞贝古城遗址,是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是在生命的短暂与虚无中,有如薇依那样,因为有了一种像耶稣基督预感到耶路撒冷即将遭受洗劫时的悲哀,所以才会为自己的不安感到几分宽慰?

就这样一路走来,当漫步在意大利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建于公元六世纪的圣·吉米纳诺(SAN GIMIGNANO)小镇,联想到彼特拉克、但丁、波提切尼、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伽利略、普契尼等人都曾在这里住过或路过时,心中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与住在巴黎的朋友聊了很久。我认为,无论哪国人,在意大利,凡不知道但丁与达·芬奇,在西班牙不知道哥伦布和塞万提斯的,就算没文化,就如在中国不知道李白、杜甫、曹雪芹一样。朋友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李杜曹与意大利、西班牙这几位人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还是远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到底要怪我们自己宣传得不够,还是怪外国人来得太少?他提到了语言。语言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文在他们看来太难了。还有什么因素呢?为什么我们对外国的了解要远比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更深入?这仅仅是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是可以囊括后两三代人的总体情况?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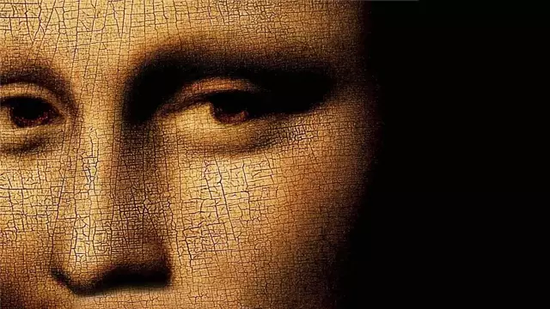
“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我真的感受到,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但似乎大家并不把文化上的触动或收获看得有多重要。在俄罗斯,我在候机回国时与一个旅游团闲聊,周围有好几个人竟然不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是何许人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我们夫妇两个人坚持进去看了一下监舍,在四周走了走,而且真的想献一束花,其他人则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候。在约旦,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与我们一道沿着崎岖的山路寻访古罗马在此的遗迹。关心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比如购物)的人太多了,手机上传播的零碎消息也太快、太杂,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讨论更多的还是“免于匮乏”与“免于恐惧”之间的关系。朋友说,我们更看重“免于匮乏”,因为匮乏的历史太久远,而且远远高估了西方人的富裕程度,但对自由和“免于恐惧”缺乏意识。其实,“自由”与“匮乏”也是一种“恐惧”。所以他认为“免于恐惧”更根本。

对此说法,我并不完全同意,觉得“匮乏”很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的实在,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程度。有比较才会有“免于”之说,而不出来走走,“比较”也只会流于空谈。我曾向几个外国人问了不该问的收入问题,月入大都在三四千欧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他们那里喝喝啤酒、咖啡,吃吃冰淇淋可以,但想旅游还远远不够。对不少外国人来说,由于社会的制度性保障好,不必为教育、生病、养老之类的事发愁。不知道这该属于“免于匮乏”,还是“免于恐惧”。
但我们心目中的“小康”,应该既包括“免于匮乏”,也包括“免于恐惧”。整个欧盟,人员自由流通,但也未见人们从贫穷地区往富裕地区迁徙的现象,因为富裕地区有富裕地区的问题,比如高昂的税收、对相应的生活技能的要求等。所以贫穷绝对是一个与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工作技能联系在一起的概念。隔着一座比利牛斯山,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聊天,这就要感谢科技,特别是微信的功能了。这方面要说发达,还真的要数中国。巴塞罗那的outlets也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宝了。

对日常生活的规训和异化
回国后,因为特殊的感情和缘由,未倒时差的我又立刻飞往正定(石家庄)国际机场,参加《社会科学论坛》杂志改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并前往参观了位于石家庄的古中山国遗址。如今这里已成一座公园,建筑宏大、雄伟、壮观。与庞贝古城相同,中山国也早已“消失”;不同的是,一个是消失于人力的征服,一个是消失于自然的威力。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所以甫在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就让攘夷狄之说大受欢迎。“古史辨”创始人顾颉刚先生更是告诉我们,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80年)至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约八十年间,鲜虞强大,建中山国号。“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县新市。”他反驳了“中山武公为西周桓公之子”的谬说,认为中山国之所在,“犹然为春秋时狄人之区域也”。在遗址中参观,能深切感受到当时的“夷狄非无文明,惟与周族文明有所不同”而已,最显著的是中山王譽墓中青铜器群的铸造工艺,数量大、类别多、做工精细,是考古学家们一致的看法。

公元前296年,赵国吞并中山国,中山国就此“消失”,比庞贝古城早了370多年。
我仔细观看了想象中的中山国的城市布局。与庞贝古城的不同,一是公众活动的场所,如露天剧场、公共浴池的缺如;二是大型石刻人物造型很少;三是下水、排水系统以及对排泄之物的处理,也远不及罗马帝国来得周密,这一点,我在土耳其、约旦等地参观古罗马遗址时也注意到了。我们的精细在器物上,双翼神兽、四龙凤方案和十五连盏灯的形体结构与铸造工艺,其精细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可惜这些东西都作为陪葬品被埋到了地下。吕思勉先生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书写于民国三十年的抗战时期。

历史迂回,时光荏苒。无论是在庞贝古城还是在中山古国,过去的、消失的,总会过去,也总会消失,但遗址还在,痕迹也有,总还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会来此参观,寄托各种复杂的感情。就像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看着刊物继续走下去,直到我们自己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无论是来自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力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