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看战国精神的形成

作者:曹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战国”条中,通过比较《左传》和《战国策》等文献,这样描写春秋时代和战国中期以后的时代区别:“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这里主要描写的是社会现象,到春秋时代为止,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温情脉脉、优雅从容的,进入战国中期以后就一下子变得冷酷无情、剑拔弩张了。顾炎武的眼光很准,从其他文献所传达的精神状态来看,也确实如此。《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及《老子》《论语》等早期文献,虽然也不乏愤慨与焦虑、批评与抨击,但其中更多的还是透露出雍容、华贵、高雅、宁静、从容、自信的气质。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通过《战国策》《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书,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战国时代的高强度与快节奏,是敢于挑战的积极姿态,是对于意志力、执行力、决断力的赞美和追求。
总之,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过去我们只能依赖战国中后期的文献来考察,而战国早期的状况,由于这一时期文献的缺失而难以窥探。现在,通过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对这一变化发生的早期进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清华简因为是流散文物,已经无法确认其准确的出土地点和考古学年代,但是通过字形和内容的比对,学界基本上倾向于将其视为战国中期以前甚至更早的作品。本文试图利用清华简所见论心与论命的资料,考察战国早期的人是如何开始崇尚个人意志、提倡进取精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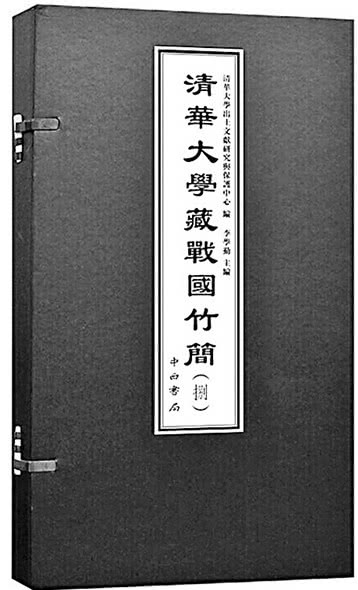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 资料图片
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册公布了一篇名为《心是谓中》的文献,虽然通篇只有七支简,但内容却极有看头。此文一上来,先强调与身体各部位(“四相”)相比,心占据中心的统帅地位。“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这是说心是人的中枢,处于人身体的中心以支配身体。“心欲见之,目故视之;心欲闻之,耳故听之;心欲道之,口故言之;心欲用之,踵故举之。”心作为身体的君主,对其他器官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接着,作者马上就将这种身心关系引申到君民关系,“为君者其监于此,以君民人”,就是说统治者如果能够借鉴这种身心关系,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心是谓中》的中间部分进一步指出:“幸,天;知事之卒,心。必心与天两,事焉果成。宁心谋之、稽之、度之、鉴之,闻讯视听,在善之麏,心焉为之。”这是说,事情的成功必须同时取决于人心和天运两方面的作用。只有沉静的心能够做出谋划、稽核、度量、品鉴,身体各个器官之所以能够采取正确的决定,是因为心在那里起作用。和荀子一样,《心是谓中》特别强调“心”具有认知的能力。但这里,作者的用意并非仅仅在于突出心的认知功能,而是通过这一功能,大大提升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的意志力可以是如此强大,甚至达到“心与天两”,与天并驾齐驱的程度。如“死生在天,其亦失在心”所示,心甚至可以决定个人的生死命运,离开心的认知作用,即便获得成功,也只是侥幸而已。虽然从西周到东周,天的垄断性地位开始逐渐下降,但到战国时代以前,天依然是对人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全能的存在,是人一切行动的规范、一切合法性的依据和保障。然而,到了《心是谓中》这里,天的地位显然降格了,天所能决定的仅仅是“幸”即偶然性而已,作者虽然不否认这种偶然性对人也具有支配作用,但同时强调,人更应该通过人心周密的思维,通过人心强大的意志,去把控事物发展的走向和结果。
即便在春秋晚期的思想家老子、孔子那里,关于心的论述还是支离破碎的,见不到对心之支配力和人之意志力的礼赞,心甚至被作为欲念象征遭到排斥。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心论突然成为诸子论述的焦点,各家都争相将心论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例如在《管子》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等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心术的具体训练方法,甚至可以看到心被分成低级的和高级的两重,即肉体的心灵和精神的心灵,道家认为只有打造出高级的心灵才有可能体道得道,真正掌控万物,成为人间最高明的统治者。上博简《凡物流形》所谓“百姓之所贵唯君,君之所贵唯心,心之所贵唯一”的说法,正是这一类心论的集中写照。在孟子那里,心成为性的载体,成为善的源泉,成为美好政治的推动者与实践者,因此,虽然名义上孟子仍然将天视为人的终极依据,但实际上孟子对通过心来实现的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强调,要远远多于他的儒学前辈。到了荀子那里,心论更是和理智成熟的认知能力、和积极有为的行动能力结合在一起,把对人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推向顶峰。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些成熟发达的心论是怎么冒出来的,现在,这一切都可以在《心是谓中》这里找到源头。
二
《心是谓中》的后半部分也非常精彩,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命运可转的重要论断。关于命运,战国以前的人基本上是两种态度,第一,如西周大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所示,相信只有极个别有德之人,能够从天那里接受大命成为人王。第二,如《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示,祸福寿夭掌握在上天鬼神手里,个体是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这两种命运观都要人向命运低头,接受命运的安排。然而,《心是谓中》却向这样的命运观发起了挑战,一方面作者不否认“死生在天”“人有天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即左右个人运命遭际的因素中有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偶然性存在,但是作者也鲜明地提出“取命在人”“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心厥为死,心厥为生。死生在天,其亦失在心”。就是说,天和鬼神并非决定人命运的唯一要素,人可以和天、鬼三足鼎立。与“断命”并列的还有人的“取命”、与“天命”并列的还有人的“身命”,“取命”“身命”就是由那颗强大的心灵操控掌握着的命运,心的作用是如此强烈,和天一样,也能左右人的生死。这样一来,命运就不是一成不变了,不是仅仅由偶然性决定了,而和必然性开始发生关联,当然,这种必然性是由人心的能动性来主导的。后来荀子之所以能够提出“天人有分”“人定胜天”,即天是天,人是人,不要轻易地把命运交给不确定的因素,人甚至应该从天那里争取有为和努力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接受了《心是谓中》一类文献的影响。后世道教甚至喊出“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黄白》)的口号,这种气概可能也是滥觞于《心是谓中》吧。先秦之后的中国人多持类似《心是谓中》的立场,既尊重天命,又认为人的努力可以转变命运,可以说这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理性精神。例如王夫之就提出“性日生日成”,认为自然禀赋都是可以转变的。
战国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格局,连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剧烈起伏,过去那种世卿世禄、按部就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的动荡,为大量有理想期待、有政治目标、有利益追求的人提供了活跃的空间和机会,因此这是一个命运的不确定性、命运的可操作性开始广受关注的时代,《心是谓中》显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此文大声疾呼:“君、公、侯、王、庶人、平民,其毋独祈保家没身于鬼与天,其亦祈诸心与身。”作者呼吁从上到下所有阶层,不要只是向鬼神、上天祈求家庭与自身平安,也要向自己祈求,就是说命运归根结底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前面论述的心论一样,《心是谓中》的命论也在高调宣扬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洋溢着一种积极、刚健、昂扬、向上的气氛。
清华简中还有一篇专门讨论命运观的文章,那就是《命训》,此文也见于《逸周书》,但过去没有多少人重视,结合《心是谓中》,我们可以对此文的价值做出新的判断了。《命训》说人有两种命,一种是“大命”,一种是“小命”。“大命”对应于“天命”,指的是天赋的、难以改变的命,与之相应的是“小命”,如“小命日成”所示,“小命”指的是人们通过日积月累可以改变的命。《命训》又说“小命命身”,即“小命”的福祸只体现在个人身上,积善累功则降以福,积不善者则降以祸。这种善与不善由德行决定,因此《命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儒家的倾向,但这种降临到个人身上的福祸可以由自己来把握的想法,确实和战国时代以前的儒家有很大不同。这种“大命”和“小命”对举的观念,在强调顺应天命的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属于自己的命运,相对于传统消极的宿命思想或极端的“非命”思想都是一种进步。
和《心是谓中》一样,《命训》也在积极论述人的命运可以改变,只不过对象成了普通百姓,即在有为君主的教导下,万民通过积善累功、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来把握属于自己的吉凶祸福。这些思想完全被荀子继承,荀子特别强调在圣王引导下,每个人通过反复地、不断地学习和修行,通过积累自身的德行,最终改变自己的境遇,从而形成一个理想社会。这样的思想奠定了汉以后两千年儒家社会命运观的基本格局,既认可不可抗拒的天命,又充分肯定个人的努力,既有所约束,又灵活善变。
总之,受战国时代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心作为欲念象征而需要加以排斥、命作为无奈象征而必须加以接受的早期观念被大大削弱,而心和命作为人主体性、能动性、意志力、行动力象征的新理念被大大强化。在清华简《心是谓中》《命训》这些战国早期文献中,我们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鲜的、活跃的气息,正是这些气息,慢慢滋养出了积极、有为、实干、刚健的战国精神。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