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阳举、朱韬:论侯外庐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2020-03-30
2020-03-30

摘 要:道教思想史研究是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侯外庐首次将道教思想史纳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使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教并立得以呈现;创建了社会史与道教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避免了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发掘在以往思想史脉络中不被重视的“异端”思想,拓展了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重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交互影响,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为道教思想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主题词:侯外庐; 道教思想史; 宋明理学; 三教思想;
原文载于《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文章内容有删节
侯外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其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为我国古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特别是侯外庐先生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以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材料,独特的视角,使当时的“思想界面目一新”,“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研究思想史、研究哲学史的人不得不读的很有权威的著作”。尽管当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多次转向,“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起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还是侯外庐的名字”。学界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卓越成就已达成共识,并对其研究先秦思想、汉代思想、经学思想、佛教思想、宋明理学思想、明清启蒙思想等课题的内容、方法、贡献都作了专文讨论。相比之下,侯外庐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的研究还鲜有人关注,这不只影响到我们对侯外庐先生学术成果、学术贡献的认识,也使国内道教研究史的回顾显得不够全面。具体到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上来说,如何在现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并寻求道教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已成为当前道教思想史研究者自觉讨论的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思考侯外庐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研究的贡献,既是对道教研究史的系统梳理,也有助于道教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深化。
一、首次将道教思想史纳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道教研究却发轫于欧洲。直至20世纪初,国内学者刘师培、许地山、陈寅恪、汤用彤、傅勤家、翁独健、姚从吾、陈垣、刘咸炘、蒙文通、王明、陈国符等先生才相继对道教进行历史学、文献学的清理,“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其中涉及道教思想的研究,但多是对道教人物、典籍孤立的讨论,没有将道教思想放置于整体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域下进行考察。
除此之外,20世纪上半叶问世的几部重量级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著作,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试图构建富有逻辑性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体系,而对于道教思想则罕有关注”。我们常常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而在早期思想史、哲学史的书写时却又或有意或无意的忽略道教思想的存在和价值,原本应该三足鼎立的中国思想缺失了一足,使得中国思想文化的很多内容都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展开。
正是有鉴于此,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撰写审查报告时才遗憾地表示:“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常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追补者也。”
陈寅恪先生认为道教对理学的产生影响深远,而且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这些都是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急需解决澄清的重要问题。客观地讲,不只是当时,即便是现在,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仍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互动问题,在十几年之后,随着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陆续出版才得以具体呈现出来。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要讲清楚道教对于理学的影响,也正是侯外庐先生道教思想研究的重点内容。
侯外庐先生认为,道教承继了“魏晋时代成了正宗”的道家思想,以宗教的形式对中国影响两千年之久,“远较道家更为深刻广泛”,因此在侯先生看来,“对道教思想的彻底检查与批判,是治思想史者不可卸却的责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侯先生首次将道教思想纳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在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写作中,道教思想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教并立得以呈现,足见侯先生的这番创举影响之大。
侯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上自东汉末五斗米道、太平道,下至宋元道教南北宗;所涉及的人物从魏晋葛洪、隋唐王玄览、李筌到宋元张伯端、王重阳、白玉蟾;所涉及的道教经典,既有此前学界重视的《太平经》《抱朴子内篇》《悟真篇》,亦有此前学界所忽视的如《玄珠录》《化书》。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侯先生注重将道教思想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如在《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侯先生将原始道教太平道的相关讨论作为葛洪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背景,同时亦强调葛洪受两汉经学转向的影响,可以视为魏晋之际“儒道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对隋唐宋元道教思想的研究,不只重视道教与隋唐佛教思潮的互动,还着重分析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同时亦强调白玉蟾对理学的吸收,揭示了儒释道三教思想交互影响的大致脉络,也充分展现了道教思想发展的复杂多变。
二、创建道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
在侯外庐先生之前,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于对于中国思想中抽象概念的辨名析理”,使他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社会史的考察,“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金岳霖先生曾这样评价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指《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者注)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我们认为金岳霖先生对胡适先生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冯友兰先生,两位先生或采用了实用主义,或采用了新实在论,都有主观臆断存在。侯外庐先生针对“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者有许多缺点”,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并指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剔抉其秘密”。如果不能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仅仅以思想解释思想,必然会充斥着大量的主观性、随意性,这种研究只能“流于附会臆度”。侯先生所强调的这些研究方法,迄今仍“是许多思想史甚至社会史学者仍然信奉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仍然是有价值和有所助益的”。下面便以侯先生研究葛洪思想作为代表,具体说明在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上如何贯彻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侯先生是较早对葛洪思想做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指出葛洪是“神仙道教在创始时期的理论与仪式的奠基祖师”,亦是金丹道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首先,侯先生对葛洪生卒年的考订,是有关葛洪生卒年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侯先生所强调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特别重视对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事迹的考证,这也是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而葛洪研究的第一个难点,也正在于史料记载的葛洪生卒年有矛盾之处,侯先生通过《抱朴子外篇·自叙》及相关史料,对葛洪的生卒年作细致考辨,以广州刺史邓岳的行迹考订为主要参考依据,认为《太平寰宇记》所载葛洪年寿61,比《晋书》所载81较为可信。
第二,侯先生从社会思潮的变化入手探究葛洪的从学经历。侯先生认为葛洪“是从汉儒法定的儒家经典入手”,但由于“汉末以及魏晋之际的学风转变,汉儒专一经守师法的严整烦琐学风已被扬弃”,所以葛洪有了广览经史百家之言的机会,最终“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侯先生指出葛洪的从学经历正是“两汉经济体制,所谓汉法度的森严被荡决以后,在思想意识界的反映”。
第三,侯先生以社会现实的动荡推考葛洪“内神仙外儒术”思想的社会根源。侯先生指出,“两晋之际,豪族内讧,民变四起,胡人侵扰。北方豪族大举南渡,江南豪族流离分化,他们都感受着脱离了户籍的‘流人’暴动的威胁”。这些尖锐的现实问题,使名门豪族一方面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宗教的安慰。“这种客观现实在思维方面的反映,便构成了内神仙外儒术的葛洪思想”。
第四,侯先生通过对葛洪时代“不稳定”的封建经济制度的分析,着力说明葛洪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往的道教学术研究,多重视介绍葛洪的道教方术和《抱朴子内篇·遐览》的目录学意义,而侯先生除对葛洪“元”本体,“元一”“真一”的修养论,神仙必有、神仙可学、重金丹、轻符箓及禳邪祈福仪式等道教思想做了剖析外,还尤其重视《抱朴子外篇》反应的葛洪政治思想。侯先生指出葛洪虽自称儒家,但其政治思想“实际上乃汉酷吏的继承,是内法外儒的‘王霸道杂之’的憧憬”。魏晋时期,曹氏采用军事屯田制的封建经济,是为维护在军事体系之下的统治权稳定,而晋的占田制仅是在此基础上作了些修改。“这种不安定的经济制度,反映在礼制与法制上的,是两汉森严整齐法度的崩溃,是魏晋清峻通脱风尚的养成”。虽然这种封建经济制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统治,但它对当时的礼制、法制埋下了动乱的祸根。曹氏代汉,司马氏代曹,拥有军事力量的名门豪族争夺权势都是这种封建经济制度的直接后果。葛洪有鉴于此,在《抱朴子外篇》的《君道》《臣节》《良规》诸篇中,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尊卑的对立应该调和,为君者只要能公正地维持名门豪族的均势,为臣者尊君尽职,“则魏晋以来的内讧篡弑都可避免”。在《抱朴子外篇·省烦》,葛洪又指出繁礼的无用,主张“删定三礼,割弃不要”,其意在于“把军事屯田时期的礼制变更,在丧乱既平之后,予以合法的确定”。在侯先生看来,葛洪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最符合于身份性地主的要求”,也是“最能适应屯田以至官品占田的经济基础”。
侯先生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葛洪思想,并多有创见,对《抱朴子外篇》的重视,也为后来的学者所依循。由于受写作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侯先生对葛洪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烙印,但他所创建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至今具有典范意义。
三、开拓道教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道教思想的研究集中在《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黄庭经》《老子河上公注》、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个别的典籍和人物。自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问世以后,道教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拓展。
(一)拓展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发掘在以往的思想史脉络中不被重视的“异端”思想,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特色之一。侯先生在对隋唐宋元的道教学术进行研究时,发掘了很多有独特价值的道教思想家,拓展了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其思想相对可以成为一种体系的”,有王玄览、李筌、施肩吾、杜光庭、谭峭、彭晓等人,对宋元张伯端、王喆和白玉蟾等道教思想家亦多有评述。这些道教人物的研究,如今已成了道教思想研究的重点,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者都认为唐代高道王玄览的思想值得关注。侯外庐先生最早揭示了王玄览的“思想渊源于道家而杂有佛家的色彩”。侯先生认为王玄览在《玄珠录》中讨论的“道”与“众生”是一是二的问题,“即出于佛学中‘佛’与‘众生’非一非二的命题”。包括“无‘众生’何处有‘道’?如‘道’是‘众生’,‘众生’何故而修道?”这些命题亦脱胎于佛教教义。王玄览又因袭老子的思想将“道”区分为“可道”与“常道”,“可道”无常,“常道”可以通过灭“知见”而修得。诸法虚妄,全无自性,“正如庄子所云,蝴蝶化为庄周,庄周化为蝴蝶,彼此全无自性”。侯先生认为王玄览的思想是承籍老庄,“而更多的是从佛学剿袭而来的烦琐的思辨”。
侯外庐先生指出,五代最有价值的道教著作是彭晓的《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谭峭的《化书》。彭晓的《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所附《明镜图》或与周敦颐《太极图》有渊源。谭峭在《化书》中“劝说上下大家一齐节俭”,但谭峭所谓的“俭”含有“不抵抗主义的意味”。《化书》的内容主要是“摹仿庄子《齐物论》,宣传泯没一切差别的相对主义思想”,但也“透露了一些暴露封建压迫剥削的思想”,内容颇有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侯先生对谭峭《化书》的重视,受到学界的关注,谭峭《化书》继而成为道教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二)开辟道教思想史的多维度研究
侯外庐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不只限于道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还涉及政治思想、逻辑思想等多个维度。这与侯先生对《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侯先生指出“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道教思想史的研究包含着道教哲学的研究,但并不等同于道教哲学的研究,这一点也被学界接受。
如在葛洪的相关研究中,侯先生便揭示了葛洪逻辑思想的价值。《抱朴子外篇》中《博喻》《广譬》两篇采用了连珠体的文学体裁,“这样用连珠体大规模的来写作,共达百八十则以上,则是颇可注意的”。侯先生认为连珠体是葛洪逻辑思想的表现形式,故而将葛洪所用连珠体总结为4种逻辑形式,并在书中加以分析。侯先生从逻辑学视角研究葛洪,受到学者的关注,至今仍被称道。
再如对李筌的研究,侯先生对李筌《太白阴经》中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思想极为肯定。他强调李筌“不但强调人事决定成败、智慧决定胜负的道理,而且有些论点涉及到人定胜天的理论”。而且李筌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只在其个人的思想中具有突出特点,亦是“道教派别里最有思想性的”。
以上略举两例以显示侯先生对道教思想史多维度研究的开辟之功。当前学界至今还没有从逻辑学视角、人文主义视角研究道教思想的专著问世,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关注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侯外庐先生对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有着长期关注。早在1950年侯先生就提出给予东汉王朝致命打击的“黄巾”属于农民暴动,而且他们是“以太平清领道作为思想行动上的指挥的”。东汉末叶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教法有相近之处,他们的教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中世纪的平等要求”;不置“长吏”而代之以祭酒,反映了宗教上的平等;“立义舍、置义米肉、令行路者量腹取足”表现了农民起义者“朴素的共产主义心态”,是“中世纪封建的财产所有制之下”,弱小的农民起义者对“生命权和生活权”的期望。《太平经》中还反应了农民起义者“反对聚敛财货而不周济贫困,主张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反对封建社会滥费的宗教仪式的观念”。但同时侯先生又强调这些反应了农民要求的教法,在和宗教理论结合的时候,“就充满着神秘的诡异之辞”。总的来说,侯先生对下层民众通过宗教的组织形式联合在一起,武力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持同情肯定的态度,但针对他们宗教组织思想的不合理成分亦表示否定。
1959年,侯先生再次探讨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他认为张角和张鲁都是农民领袖,并称《太平经》为“农民道教经典”,东汉以后以道教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张岂之、李学勤、杨超等先生所著《中国历代大同理想》接受了侯先生的观点,亦认为《太平经》是“农民道教的经典”。侯先生对道教和农民起义关系的持续关注,得到了当时学界的响应,相继有学者对《太平经》提出了较高的评价,杨宽发表《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将《太平经》的阶级属性问题推到了极端,激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推动了《太平经》的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繁荣。
四、重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交互影响
陈寅恪先生对时人忽略道教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无视道教思想对理学的影响,深感遗憾。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只重视辨析道教对理学的影响,而且将佛教对道教思想的影响,理学对于道教南北宗的影响都视为研究重点。
(一)佛教对道教思想的影响
侯外庐先生认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是“禅观”的翻版,同时也指出《云笈七籤》所收录的修炼方法,“大体不出《坐忘论》的范围”。侯先生不仅指明了作为唐代高道的司马承祯其思想有佛学渊源,还提示了佛教思想对后世道教修炼方法亦有深刻影响。
张伯端是北宋道教的代表,侯先生指出张伯端所作《悟真篇》是“宋代道教接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最早的例证”。侯先生认为张伯端的著作表达了当时一般流行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悟真篇》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撮合三教”,篇中所附《禅宗歌颂诗曲杂言》可以明显地看出对禅宗思想的吸收融摄。
(二)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道教如何影响宋明理学,是侯外庐先生对道教思想研究的重点,并一直将对此问题的关注延伸到《宋明理学史》的写作,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重点、热点。
《宋明理学史·绪论》这样写道:“道教思想的渗透(指对宋明理学的渗透——笔者注)也很清楚……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受道教影响较多。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说,当也受道教的影响,朱熹著《参同契考异》,是明显地在关心道教的经典。”侯先生认为道教思想对宋明理学的渗透,是宋以后学术思想领域的大问题。“如果没有道教的长期发展,没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论究如‘太极’‘先天’等《易》学问题的情况的。”
侯先生赞同《西山群仙会真记》为晚唐施肩吾所作,明确指出施肩吾所谓的“‘从道受生谓之性,自一禀形谓之命’已开后来道学家的先声”,对于“道”“气”并举的提法也为“后来道学家的张本”。施肩吾所谈的“道”“器”问题,在后来的道学家著作中数不胜数,虽然施肩吾对于“道器”“体用”的问题没有详细发挥,“但已建立下命题的雏形”。
侯先生还指出杜光庭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杜光庭所谓“得清明冲郎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其意指人禀天地之气,但由于所禀气不同,而有了人的贤愚贵贱之分,“这和宋代道学家理论也是非常相似的”。
侯先生还怀疑张载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可能并不是张载的独创。与张载同时代的张伯端有“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的说法,与张载所言几乎相同,但张伯端“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互关系的论述,却不如张载讲的那么深入,很可能张载受了他的影响”。
周敦颐的思想受道教影响很大,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先生辨析了北宋象数学的传统,他指出周敦颐与北宋高道陈抟有师承关系,并认同毛奇龄所说的《太极图》是模仿了彭晓的《明镜图诀》中的《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在《宋明理学史》写作时,又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所收的《太极先天之图》再次作了详细的对比,并将周敦颐《太极图》传授的几种说法作了细致的考证,最终确定“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传自陈抟”。
侯先生在对二程的研究中,亦指出二程“所讲‘道’的范畴更通向老庄以至道教”,二程所认为的有一种特别的“气”,即“真元之气”的说法,“无疑地是受了道教胎息说的影响”。
不只二程代表的洛学,“蜀学学者也讲求道教方术”。苏轼8岁便以道士为师,“他写了不少《龙虎铅汞论》一类的道教文字,实际上也确曾‘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苏澈自称“心是道士”,秦观“也有修真遣朝华的故事”。
理学、心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王阳明与道教皆有密切渊源。侯先生指出“朱熹与道教接近当受蔡元定的一定影响”,二者关系亲近,曾共究《周易参同契》。而且朱熹还曾假托“崆峒道士邹 ”,对《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作注,“凡此俱可证明朱熹对道教的崇信”。王阳明与道士往来的事迹,大家更是耳熟能详,阳明龙场悟道,“也与神仙家的神秘的求道术有关”。
(三)理学对道教南北宗的影响
侯外庐先生指出,道教北宗全真道除了受禅学的影响之外,在三代弟子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如王志谨《盘山语录》所谓“看念虑未生”,是理学所谓“看未发之中”的同义语。尹志平《北游语录》中,所说的“人性去道不远、天赋性命、性中之天等命题。也都不难看出道学的痕迹”。
侯先生还指出道教南宗与朱熹也有一定的关系。南宗实际创始人白玉蟾对朱熹深为倾倒,在朱熹学说被视为“伪学”遭禁的时期,白玉蟾“化塑朱熹遗像”,并为之作赞。“从思想上考察,道教南宗的理论乃是道教、道学、禅宗三者的混合物”,以白玉蟾《无极图说》为代表的南宗修炼方法是“仿照着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撰写的”,“白玉蟾的再传弟子萧廷芝的《无极图说》更直接采用了《太极图》”。分析白玉蟾《无极图说》的实质,“可以视为朱熹的人性论和修养法的道家版”。白玉蟾所谓“性”“命”,相当于朱熹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朱熹所论的以“天命之性”驾驭“气质之性”,在白玉蟾那里被改称为“以神驭气”。在对白玉蟾思想深入分析之后,侯外庐先生作了一个深具启发性的总结:“道教本来是宋代道学成立的凭借之一,然而通过在道学中与儒家思想、佛教思想的融合,又产生了新的道教宗派,以白玉蟾为代表的道教南宗就是这一交互影响过程的显明例证。”
以上足可见侯外庐先生对儒释道思想交互影响的重视,且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见解,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如今三教思想的交互影响,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对佛教如何影响道教,道教如何影响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又怎样影响了道教南北宗,学界的论文和专著都已经很多。但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三教思想的交互影响多集中在对个案的关注,没有从整体的中国思想史脉络上揭示三者相互影响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学者囿于学术立场偏见,专治一教一家者往往强调“自家”思想的“原创性”,而极力辩称“自家”思想未受“他者”影响,仅仅突出思想传播的“单向性”,使三教思想的交互影响研究难以客观、真实地深入下去。而侯外庐先生所秉持的研究方法、研究态度能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客观、真实的参考,进而深化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自侯外庐先生将道教思想史纳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后,道教思想史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书写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侯外庐先生所关注的很多道教人物、典籍以及相关问题如今已经成为道教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点、热点,这无疑也彰显了侯外庐先生的远见卓识。总结侯先生对道教思想史研究的贡献,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人的学术遗产,对我们今天的道教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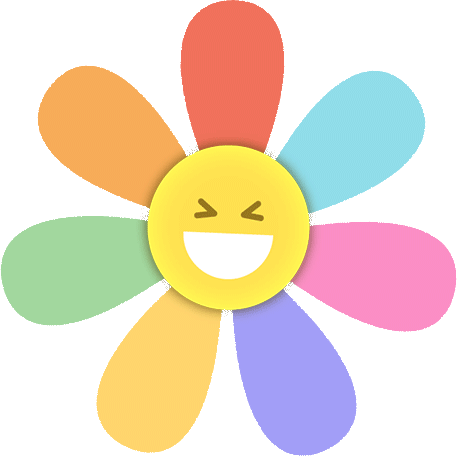
谢阳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韬,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2018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