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取消,新书难产,海外出版业冲击波对国内影响几何?
 0
0
如果不是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全球出版业不会感到如此命运相连。
2月,在国内疫情最为吃紧的时候,海外出版业最关注的是中国印厂何时复工,因为各大出版商都面临新书推迟,尤其是漫画、杂志类出版物。3月出街的一些日本杂志不得不以没有附录的方式发售,而没有附录意味着销量堪忧。
如今国内印厂已经有序开工,但随着疫情在海外以几何级数蔓延,全球出版业正被强制按下“暂停键”——书展取消、活动中断、印厂停工、书店关门——虽然国内正在复苏,但海外冲击波却正在传导回来。
每年春夏本应是出版业洽谈交易的最繁忙的时段,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疫情正在让这一切“冻结”——伦敦书展取消、博洛尼亚书展延期,莱比锡书展取消,巴黎书展取消——一日一变的疫情动态打乱了所有出版商的计划表。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出版就是publicity,是一个公开传播的工作,主要靠聚拢人气,靠面对面的书展、促销会、新书发布会,现在突然一下子不能‘会’了。隔离把病毒阻断了,也把我们出版人的联络阻断了。”安德鲁·纳伯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黄家坤告诉做書。

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
当然,从一开始的猝不及防到后来的积极应对,海外的出版商正在快速适应“书展无限期停办”的新常态。
“今年的伦敦书展虽然取消了,但有一些出版社,比如企鹅兰登旗下的两个出版品牌,会发来短视频,把策划编辑邀请到镜头前来推荐重点书。大部分同行还是通过线上分发书目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在正常进行选题评估、报价。”磨铁图书欧美版权负责人高蕙表示,他们与版权合作方的联系并未受太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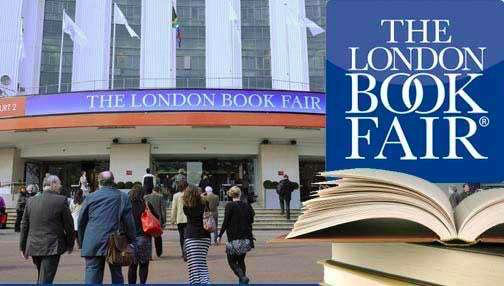
但是,书展作为全球出版人交流、联谊的“行业派对”的作用,却是邮件和Zoom无法替代的。做書曾经报道过,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整座城市的酒吧里都挤满了编辑,据说酒吧的成交率远高于书展本身。
黄家坤坦言虽然疫情令全球出版业快速完成了合同的电子化,但对她个人而言,线上交流的体验并不好,“能够完成的只是一个basicly的沟通,肯定不如坐在一个物理环境中,旁边人来人往,各种漂亮的站台,各种酒吧。”
理想国版权负责人揭志勇也表示,虽然能够收到新书书讯和目录,但见面沟通无疑会更丰富一些,新书的资讯也更立体。
“全球同行对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还是很有期待的,如果能如期举行,可能会迎来全球版权贸易市场的一个小高峰。”然而,除了疫情能否在10月之前成功控制尚属未知数以外,下游的“停摆”正在减缓所有新书的出版节奏。

虽然作家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作(连“拖稿大王”乔治·马丁都在疫情期间每日赶稿),但出版商却正在变得越来越谨慎。疫情结束之后,文学代理商可能会被新的书稿淹没,到那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出版商来消化这些书稿。
对于海外的出版业来说,目前最棘手的难题,来自于神经末梢——书店的生死存亡。3月23日,挺过了连锁书店、网上购物、电子书等多次冲击的纽约文化地标Strand书店宣布裁员188人,仅留下24名员工。可以视为疫情之下书店困境的一个缩影。

上周,做書曾经关注过那些因为疫情被耽误的书,这个问题在图书电商、直播等并不发达的欧美更加突出。由于越来越多的书店关门歇业,新书几乎不存在任何推广的机会。
对于很多作者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书籍的宣传机会,更意味着与社区的连接被切断。美国诗人乌兰达·巴雷特对《出版人周刊》表示“作为一名残障自由职业者诗人,我正在失去与社区的联系,无法与其他优秀的酷儿,跨性别,残障人士和有色读者群体进行专业交流,也没有扩大听众的机会。”
独立作者伊丽莎白·斯廷齐两本新书的营销、宣传活动都被取消了,以至于“我未来职业的形态可能会永远改变。”
当然,海外的书店也在积极展开自救行动。哈珀·柯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打出整版广告,为独立书店摇旗呐喊,鼓励顾客从独立书店购买。无论是否已经关店,各家书店都号召顾客到官网去下单,很多本地书店除了官网外还接受邮件和电话预订。
美国版“孔夫子”Bookshop.org宣布,疫情期间将独立书店的分成比例提升到30%。2月份Bookshop.org的销售额增长了400%,向独立书店的分成高达10万美元。
相比之下,国内实体书店在渠道中的日趋“边缘化”,反而使出版业没那么容易感觉到神经末梢的“切肤之痛”。
不仅如此,海外出版节奏的迟缓,新书的“难产”并不会那么快传导到国内,目前最令国内出版品牌头疼的仍然是那些“老问题”。
“整个出版节奏稍微有点变慢,但疫情不是主要因素。”高蕙告诉做書。

3月12日,《聊天记录》译者钟娜在写给literary hub的一篇文章中,采访了“纸上造物”等出版品牌,介绍了疫情对于中国出版业的影响。她惊讶地发现:出版业面临的都不是新问题,“出版一本外版书,尤其是美国作者的书正在越来越难,疫情只不过是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